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虚拟偶像正在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文娱产业的新热点。技术驱动下,虚拟偶像从最初的虚拟歌手拓展至虚拟主播以及人工智能虚拟偶像,样态日益多元。后现代消费主义粉丝文化狂潮下,偶像粉丝生态呈现拟象化趋势,为虚拟偶像的兴起提供了文化土壤。相比真人偶像,在技术想象力下,虚拟偶像更真诚、全能、专属、亲密。然而虚拟偶像的价值实现需要技术支撑,未来的虚拟偶像应当借助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成为能够实现沉浸式交互的智能化人格化偶像。在讨论虚拟偶像的技术发展范式时需反思技术的合理性。
原文信息
试论人工智能时代虚拟偶像的
技术赋能与拟象解构
喻国明、耿晓梦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1期(第23-30页)
原文链接:
http://shjx.cbpt.cnki.net/WKD/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shjx
关键词:虚拟偶像;粉丝文化;拟象;人工智能;虚拟现实
并不算年轻的虚拟偶像市场再度受到强烈关注,动漫IP、游戏厂商、互动社区、通讯巨头等各方力量纷纷入局,虚拟偶像大有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文娱产业焦点的趋势。“虚拟偶像”一词早在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就已出现。但直至今日,对于“虚拟偶像”还未有十分明确的定义,究其原因,伴随着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成熟,虚拟偶像样态持续演进,技术对虚拟偶像的形塑仍在进行中。虚拟偶像,从字面上理解就是非真实人类偶像。虚拟,并非客观存在的人物实体,是依托现代影音技术和手段的无真实本体的虚构形象;偶像,不同于小说、电影、漫画中构建出的具有故事叙事色彩的人物、角色或形象,通过媒介与受众形成交互,行为设计符合大众需求和追爱。概言之,虚拟偶像是在人工智能时代互联网等虚拟场景或现实场景中进行偶像活动的架空形象,包含了技术手段和运营模式两方面的表征:在技术手段上,利用计算机图形、语音合成等手段人工制造“能说会唱”的虚拟存在;在运营模式上,仿照真实偶像进行演艺活动和开展形象运营。虚拟偶像的兴起与发展得益于技术手段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也离不开造星工业体系的成熟。
与持续高涨的市场热度对比,国内外研究者对虚拟偶像的关注稍显不足。目前国内外多数研究是围绕着“初音未来”这一典型个案展开,也有国内研究者将研究对象拓展至本土偶像“洛天依”,但缺少对虚拟偶像整体生态的把握。在这些个案研究中,粉丝群体在虚拟偶像生产消费中的生产者功能以及自组织性等话题成为研究者重点探讨的话题。总体来看,已有研究虽然在虚拟偶像的最新技术形态演进与中宏观产业体系解构等方面稍显薄弱,但也启发式地指明了未来研究可以借鉴的理论工具——迷及迷文化。迷(fans),又被译为“粉丝”,作为最积极的受众,一直受到学术界关注,迷研究成为媒介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热点。迷有电视迷、游戏迷、股票迷等等,都是入迷行为的一种;在娱乐工业语境下讨论偶像时,最常使用的名词还是“粉丝”。如何理解虚拟偶像兴起的必然性?虚拟偶像的价值何在?虚拟偶像离现实还有多远?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关系着对虚拟偶像的属性认知。本文结合迷理论,从技术与文化的双重视角,就虚拟偶像的驱动引擎、重要价值以及关键技术要素展开探讨,以期为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个现象级存在——虚拟偶像——的动力系统、价值逻辑和未来发展路线提供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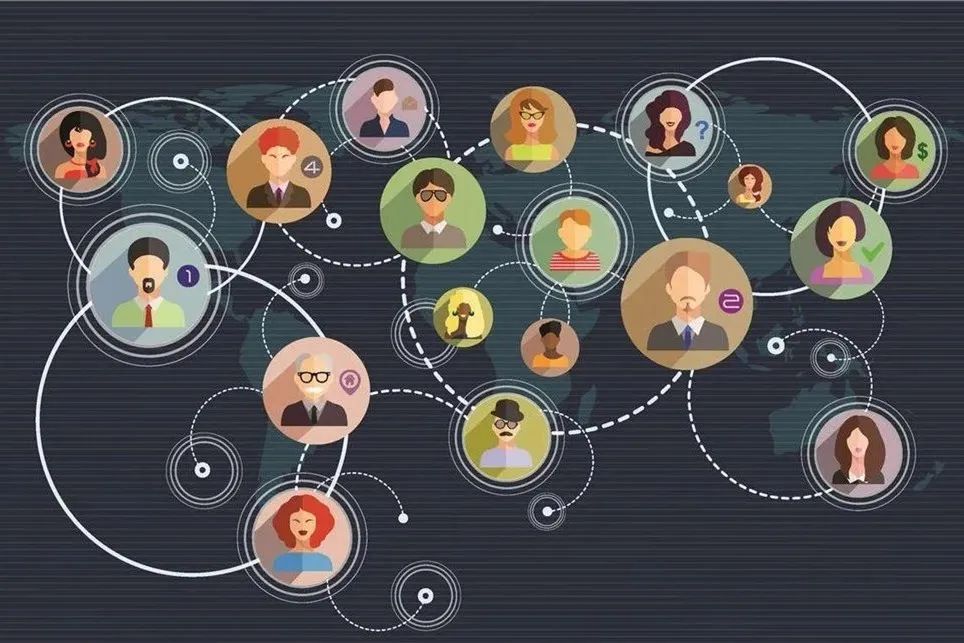
技术引擎:技术驱动下
虚拟偶像样态持续演进
虚拟偶像的前身可以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George Stone等人创造了一个由计算机合成的名为Max Headroom的虚拟人物,爱范儿.虚拟偶像,而虚拟偶像的概念则是在日本诞生与孵化的。20世纪80年代就有公司提出“培育国民级虚拟偶像”的企划;1999年,第一个计算机图形(CG)虚拟偶像“伊达杏子”诞生,但因为当时CG建模技术尚不成熟,3D模型的虚拟偶像在美感上仍逊色很多。整体来看,在进入21世纪之前,虚拟偶像仍处在文娱产业的边缘地带,并未受到大众的关注。真正将“虚拟偶像”这个词带入人们视线的是诞生于2007年的初音未来。初音未来其实只是日本音乐软件公司CRYPTON以雅马哈集团第二代VOCALOID语音合成程序为基础开发的音源库。依托于语音合成技术以及音源库,在初音未来前后诞生了一批虚拟偶像歌手。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虚拟主播作为新一代虚拟偶像迅速兴起。虚拟主播的典型代表,是全球第一Vtuber“绊爱酱”。虽然绊爱反复强调自己是AI人工智能ÿ








 本文探讨了虚拟偶像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驱动下如何从虚拟歌手发展到虚拟主播,以及人工智能如何赋予虚拟偶像更真实、全能、专属和亲密的特性。虚拟偶像的兴起源于数字技术进步,如语音合成、3D动画和人工智能,它们提供了沉浸式交互的潜力。文章还讨论了后现代消费主义文化下粉丝生态的拟象化,以及虚拟偶像如何满足粉丝对理想自我投射的需求。未来,虚拟偶像将依赖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技术,以实现更高级别的沉浸式互动和个性化体验。
本文探讨了虚拟偶像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驱动下如何从虚拟歌手发展到虚拟主播,以及人工智能如何赋予虚拟偶像更真实、全能、专属和亲密的特性。虚拟偶像的兴起源于数字技术进步,如语音合成、3D动画和人工智能,它们提供了沉浸式交互的潜力。文章还讨论了后现代消费主义文化下粉丝生态的拟象化,以及虚拟偶像如何满足粉丝对理想自我投射的需求。未来,虚拟偶像将依赖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技术,以实现更高级别的沉浸式互动和个性化体验。
 最低0.47元/天 解锁文章
最低0.47元/天 解锁文章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