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收录于信息社会50人论坛2022年论文合集《寻路:信息社会新格局下的选择》,中国工信出版集团,2022-11,pp123-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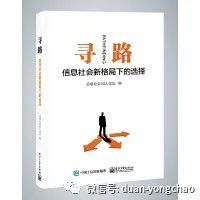
技术的喧嚣与思想的隐忧
段永朝
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元宇宙”成为引领数字时代先河的头羊。一时间,各种预测未来大变局、大转型和大危机的文本甚嚣尘上,仿佛天翻地覆的巨变近在眼前。伴随这种躁动情绪的,其实是对未来深深的不安,以及某种难以察觉的“大忧虑”,我称之为“旧世界最后的盛宴”。
元宇宙:旧世界最后的盛宴
这里有三个关键词:“盛宴”、“最后的”和“旧世界”。
从近两年参与元宇宙讨论的各界人士来看,这无疑是一场“盛宴”,人们视元宇宙为正在兴起的风口,所有人都不希望错过。那为什么又是“最后的”呢?我是想表达这样一层期望,期望元宇宙不要再度演变成一场话语狂欢和资本盛宴,不要被“玩儿坏”了。
第三个关键词是“旧世界”。今天人们的生存状态都处于旧世界的束缚当中,旧世界给我们带来的烙印难以消除。借老子讲“日用而不知”的话,我们今天是日“处”而不知。每当我们以为已经一只脚迈进了新世界门槛的时候,登高一望却发现自己依然处于旧世界。
今天大家所讲的元宇宙有几个特点:韭菜、圈地和泡沫。但这还只是“小忧虑”,也可以说是“发展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这种忧虑只是在思考元宇宙是不是新一轮的商机。在思想层面争论这些事情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尚未遭遇大忧虑。
凯撒大帝[1]曾讲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想看到的东西,我们看到的只是让我们看到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下,我想总结元宇宙的三个关键词:感知、想象和秩序。
首先是感知。过去10年间,我在各种演讲和授课中,对互联网、数字时代的讲述,有一个主题叫做“认知重启”。它的底层逻辑已经在元宇宙中涌现了,我把它叫做“六根重塑”。
人的感官是我们跟这个世界打交道唯一的通道:眼、耳、鼻、舌、身、意,中国人耳熟能详。但是我们的感觉系统正在被智能技术重塑,就像过去十年来我们被手机重塑行为一样。很多人每天平均花费6个小时在手机上,做的无非是两个动作:刷屏和扫码。可见技术对人们感知的影响有多么深刻,而且这不过是刚刚开始,还很难预料未来对感官重塑发展到何种地步。
比如这些年讨论赛博空间(Cyberspace)时,反复被提到的“身份”问题,我认为只是幼年时期,真正的问题是重新塑造“数字人格”,是“数字生命”的问题。我在北大的课堂上给孩子们讲,你们这代年轻人将来碰到的最大的心智挑战是“人有八条命”:除了一个肉身生命之外还会养育七条数字生命,而且每一个数字生命都独立于你具备了数字人格。请问你能hold住吗?你hold不住不怪你,你“是不是能hold住它”完全取决于有没有支撑它的一套话语体系/思想体系。
第二个关键词是想象。近几年在区块链圈子里,讨论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质化代币)异常火爆。当我们谈论这样话题的时候就跟五年前讨论人工智能一样,我们会发现很快出现选边站队,世界马上分成两类人:乐观派和悲观派。仔细想无论是乐观派还是悲观派都身处在同一个世界,都深受同样的低维度认知的困扰。所以“想象”是对人的重大挑战。我们如何想象高维空间?如何认知高维空间?这是今天摆在所有的程序设计员、企业家、政治家、每一个村姑小妹面前的共同问题。
第三个关键词是秩序。关于秩序,朱嘉明[2]老师曾在谈到元宇宙时,提到有三次大变革、大转型:轴心时代、文艺复兴、工业革命。这三个时代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这三个词语的诠释都来自西方话语,都不是原生思想。这种历史思维不是我们文化母语的样貌。我想问的是,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对“秩序”这两个字的理解,是否一开始就陷入了话语“失衡”?从今天我们花大量笔墨来争论元宇宙的一些所谓问题开始,我们可能就陷入到这样一种被编纂的“他者”境地。
理解世界的三个模型
西方文化的母题,在那幅著名的西斯廷教堂天顶画中有直观的表达。这是米开朗基罗[3]的作品,呈现上帝和人的关系。我们在学术研究、课堂教学和日常交流中每每使用“上帝”、“悲剧”这些术语,还包括“宇宙”和“世界”等,这些术语背后携带的血肉是我们不熟悉的。我们看这幅天顶画的时候内心会奔涌出一种莫名的悲悯吗?会奔涌出来一种渴望上帝的眷顾,感受到那两个手指将碰却没有碰到一起的刹那间的那种惆怅吗?可能不会。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很难理解在上帝观念之下,为什么西方人会把存在物看作是一个“巨链”[4]?有人可能认为这和东方婆罗门教、印度哲学所讲的那样一幅三十三重天的观念是如此相似。然而细细想下去,其实这两种关于宇宙的想象,关于宇宙层级的想象大有不同。这种对宇宙的秩序的想象,是西方万物理论的雏形,这一雏形某种程度上支配着西方思想的想象。
这里简单讨论三个“世界模型”。

首先是古罗马普罗提诺[5]著名的“喷射说”:光线来自至高无上的The One,唯一的亮点;这个光线普照大地养育万物。这一点和东方完全一致。但是“喷射说”更重要的是强调存在生命的上升和下降通道。普罗提诺的模型中所有人都居于中间一层,再往下依次生命力由强而弱,直至无生命的层级;由人这一层向上,是天使、先知和神的层级。喷射说的思想基础是,人的灵魂受到玷污而堕落了,所以命运跌宕起伏,这是一种生命的遮蔽状态。然而正是对这种人的生命状态的觉醒,导致普罗提诺也被贴标签作为“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认为通过太阳光芒的指引,人的灵魂有可能逆向升华——灵魂的拯救和净化。我认为普罗提诺的叙事要分成两半:第一半是“万物生长靠太阳”,这一点东西方皆然。但是另一半有温度的,有情感寄托和寓意的“堕落和拯救”的叙事,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普罗提诺为圣奥古斯丁[6]扫除了障碍,所以奥古斯丁完成了古希腊思想和古希伯来思想的合流。这是第一个世界的模型。

第二个世界的模型来自著名的英国哲学家波普尔[7]。1978年波普尔在名为《客观知识》的演讲中划分了三个层级的世界:物理世界、心理世界和观念与文化世界。重要的是波普尔的这三个世界是“壳状”的,每一层都包裹着下一层,而且包裹得非常密实,密不透风。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综合了笛卡尔的心物二元、康德的客观知识和对自在世界的追求。但这一模型其实是对西方知识体系的巨大挑战,这个模型将会毁灭普罗提诺世界用于灵魂拯救的那个上升通道。这是西方文明在近300年启蒙运动之后遭遇的“大忧虑”,这个大忧虑越来越以反思理性至上、批判工业资本主义、探求人的精神解放的新可能的方式,以及最近30年互联网、智能科技、数字经济的方式呈现出来。

第三个模型由王飞跃[8]提出。王飞跃在2004年从复杂系统研究的的角度提出ACP模型[9](人工社会、计算实验、平行执行)。这一模型综合了控制论、系统论、自组织理论、模型论和社会经济系统的思想,将智能技术视为社会经济运行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既分析又综合。在今天元宇宙的氛围之下,我认为这个模型恰恰展现了东方的智慧。这也应合了朱嘉明等多次提到的关于“大危机”的论断:人类今天再也折腾不起了,今天的物理世界再也不能用如此高昂的代价做无休无止的实体实验,不能为了探索更好的社会组织架构、更好的生产方式在这个肉身世界里面做这样那样的实验,等待一个优化的结果在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后发生。
王飞跃的世界模型改造了波普尔的世界模型,非常难得地突破了波普尔三个世界之间密不透风的包裹状态。他捅了一个窟窿。这个“窟窿”是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人工世界。所谓纯天然的自然世界已经一去不返了。事实上自从人类学会驯化物种进入农耕文明,自从人类学会扔石头、打棍子的石器时代,人类就进入到一个跟自然彼此驯化的新阶段。只是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理性主义高扬,带来一个“恶果”,就是我们不承认这一点,我们总以为自己在遛狗,从来不承认狗也在遛我们。今天数字世界的最大启示,就是我们必须承认“人遛狗和狗遛人”是同时存在的、并行不悖的世界状态。从这个角度看,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等等方式,只不过是在推动狗遛人的世界快速地发生。
如果在不同的物种层级之间重新找回自由跃迁的通道,那就意味着堕落为魔鬼和成就为天使,具有同等的可能性。这样一来,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将会等量齐观,拥有同样的权重。在价值判断的问题上谁战胜谁,谁为主、谁为辅,谁更有优先权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这种虚实交互、虚实纠缠的世界,将会带来何种新的世界秩序?反过来这也为我们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更高的挑战”就在于我们可能不得不深入思考“新世界和旧世界”的表述方法,不得不检讨我们思考整个世界所使用的思想框架,是不是出现了极大的盲区和眼障?
比方说像葡萄酒的叙事中,新世界葡萄酒的寓意是“调制”,即工业化的生产;而旧世界葡萄酒的关键词是“酿造”。旧世界押上的是时间代价,愿意通过“耐心等待”“被动等待”,让事情自然发生。新世界的人们已经不愿意等了。他们恨不得明天一步跨入到一种非常光明的、和谐的、人人平等的和自由的世界,他们开始用技术的手段干预这个世界的节奏,介入世界的演化。这一点对人类启示并不陌生,但在数字时代里,这种技术对世界的干预、对生命的介入,有了全新的意蕴,已经完全不能采用过去的思想范式。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正处于一种深深的“眼障危机”,这个眼障危机在于互联网计算机和虚拟世界已经让一个我们过去熟悉的、沿着时间线实时展开的物理世界演变成了一个空间上并发的世界。但是我们浑然不觉。更要命的是在这个并发的世界中,大量的数学算法在为它佐证。所以我们今天最大的忧虑是我们的欲望似乎是可以遍历的,我们可以足不出户遍吃百味、遍览天下,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想象到今天这种并发的情境意味着什么。所以所有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装备和数字世界美好蓝图都包含着这样的隐忧——世界将会变成一个鸡笼世界。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鸡笼世界的边缘。
简单的回顾过去二百年来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打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用的方法,就可以多少感受到“他们把我们坑了我们都不知道”。

第一波“数字化”用统计数学打造了所谓“正常人的社会”。18、19世纪概率统计大行其道的时候,无论是统计学家、地理学家,还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都在使用统计学方法背后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假设了一个“正常人社会”的存在。通过抽样数据分析,得出对社会人群中人口统计、经济统计、健康状况、心理测评、口味偏好等等的“社会学画像”,从而捏造出某种“平均人”的形象,将这种平均人视为“正常人”。一切偏离这一画像的人都属于需要行为矫正、心理治疗的“另类人”。这恰恰是社会分崩离析的开始,但是学者们和政治家们当年不以为然。一切社会治理的努力方向都在于驯化那些“不正常的人”,包括福柯[10]讲的精神病院、军队、监狱、学校等等,也包括现代生活中的职场。

第二波“数字化”就是当下炙手可热的智能时代。有一句话揭示了数字时代的技术信仰:一切皆计算,代码即法律。“一切皆计算”的思想根源在于阿兰·图灵[11]和他的老师邱奇[12]以及另外一位物理学家戴维·多伊奇[13]给出一个命题:一切计算过程都能用图灵机来实现(包括量子计算)。将世界的运行秩序归结为计算问题,是西方数学思想中的一条绵长的暗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柏拉图,追溯到霍布斯、莱布尼茨、拉普拉斯。现在天下所有人都信以为真,奉为圭臬,但这背后没有更大的隐忧吗?过去五年人工智能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观赏着各种千奇百怪、令人瞠目结舌的表现。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人工智能表现良好背后的隐忧是它的不可解释。
为什么“可解释的AI”如此重要?
AlphaGo可以战胜世界顶尖围棋高手,但是它从来没有告诉你它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此即“人工智能的可解释问题”。可解释的人工智能(Explaina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XAI)来自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在2016年提出的一个说法,指的是可以提供细节和原因,使得智能模型能够被简单、清晰地理解。从半个多世纪以前提出量子计算的概念,到最近几年谷歌等公司推出量子计算机,使得XAI问题更加紧迫。但迄今为止,似乎一众物理学家都无法很好解释什么是量子!在这个问题上我只钦佩费曼[14]的老师惠勒[15],他虽然没有得诺贝尔奖,没有被加持过,但是他讲的“万物源于比特(It From Bit)”是一个将影响未来千年的重要思想。

这个世界的底层结构,既有可能并不是像我们的肉身所感知的那样,是一个连续的、光滑的几何所描绘的;有可能是不连续的,是“一跳一跳”的,是“一抽搐一抽搐”的。我们过去认为这种“一跳一跳”的状态是对连续世界的采样,是连续世界的某种“模仿”。
最近几年,人工智能界在探讨“可解释的AI”这个重要课题,但社会公众对这件事情似乎并无多少感知。这是个问题。举一个例子,有机构将“大模型”列为2022年度值得关注的技术前沿趋势之一。何谓“大模型”?通俗说,就是智能模型中的参数数量达到或超过惊人的数千万、数亿的量级。比如2020年5月美国一家名为Open AI的人工智能公司,推出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GPT-3算法,其中用到多达1750亿个参数,这让机器学习的效果突飞猛进,也让人瞠目结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假以时日,这些疯狂算法会撰写越来越多的报告、论文、小说、诗歌,而且水准丝毫不亚于专业的高级文秘、咨询顾问、科研工作者、作家和诗人。
这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被抛出来,一定会有一大波所谓观察家为受到惊吓的吃瓜群众解释“这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但是,我这里说的并非这个意思。我是说,当这些蛮力算法、疯狂算法在不 知疲倦地生产“内容”、“观点”、“意见”,甚至“忠告”、“判断”、“选择”的时候,对那些算法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算法自己当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关键是算法工程师自己,其实他们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那么问题就来了:假如算法自己不能“解释”自己,算法工程师其实也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些喋喋不休的观察家、评论家、主播、博主、意见领袖,凭什么觉得自己能解释得了这个问题?
这就是我觉得需要先静下心来,认真思考技术背后的思想、哲学乃至文化的根由。
互联网商业化近30年的历程中,人们已经充分感受到互联网、智能科技对日常生活、经济生产和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然而,这种影响除了“速度进一步加快”,我们还应该警觉到什么呢?
最近5年,智能科技领域中的单一技术已经向聚合的方向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等,基本被“元宇宙”这个概念包笼。如果再加上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神经科学和脑科学、能源技术等等,这个世界的“巨变”“剧变”“聚变”应该是毫无悬念的。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它对人的影响有多大,而是人会在这样的“jù变”中发生何种内在的变化。
美国畅销书作家温伯格[16]2019年出版的新书《混沌:技术、复杂性和互联网的未来》,将思考的焦点对准这场前所未有的“jù变”在底层逻辑上带来的认知重塑。作者认为,确定性的世界无可挽回地被不可预测甚至不可解释的新世界替代。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和意义,是人与自己的创造物共生演化的内在动力。
用大众语言重新翻译一下温伯格的观察就是:我们将面临一个“没有答案”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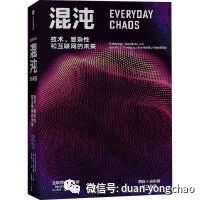
对数百年来被工业思维和工业产品滋养、塑造的人们来说,这个世界是确定的、“有答案”的,这不仅是世界有条不紊运转的前提,也是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支撑。可以想象,假如人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没有确定的答案”,或者“不能肯定所知道的这个答案,是不是靠谱”的世界,那么人们内心的失落、沮丧、惶恐、迷茫,甚至抑郁、绝望将会多么深重:就像天塌了一样!
对因果的迷恋和对确定性的追寻,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然而,这并不是一点儿疑问都没有。
没有答案,不等于没有思想
美国哲学家杜威[17],1929年在爱丁堡大学的演讲就以“确定性的寻求”为题,把人们对确定性的偏爱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10年前,以色列70后历史学家赫拉利[18],以《人类简史》一书奠定了他全球畅销书作者的地位。在这本被译成45种语言的书中,赫拉利用惊人的口吻写道:农业社会是一个巨大的骗局。
为什么这么说?赫拉利给出的解释是:定居。
一万年前的定居生活,让物种驯化成为耕作农业和畜牧业的基础。漫长的物种“驯化”史,不经意间将“定数崇拜”深深地刻写在人们的肌肉记忆中,刻写在人们创造的神灵、祭祀的观念底座上。
今天的互联网和智能科技,将再次从底层改变这一切。
温伯格 20 年前和哈佛伯克曼中心的道克・希尔斯[19],还有另两位作者,共同撰写了著名的《线车宣言》。这部气势非凡的著作,直接模仿1517年被马丁・路德[20]张贴在维滕贝格讲堂门口的《九十五条论纲》,对工业时代的组织模式、市场模式、营销理念发起了猛烈的批判。比如宣言中的第一条,就是这样一句明快的语言:“市场就是对话。”20多年后,这句话依然 振聋发聩,发人深思。元宇宙、区块链、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市场,不再是商家向消费者“填鸭”“喂食”式的倾泻商品,不再是“买买买”;消费者也不再是待“宰”的羔羊,被动的消费者,不再是“我买故我在”。那么这种“对话”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显然不是那种伪装在“推荐算法”里面的“大数据杀熟”,也不是那种不停地渲染“焦虑”、“创造需求”的消费者精准营销。那是什么呢?在静心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放下的,是对确定性的迷恋。
温伯格和很多我们熟悉的数字思想家,比如托夫勒[21]、尼葛洛庞蒂[22]、彼得・蒂尔[23]、凯文・凯利[24]等一样,是互联网商业化以来的30年中为数不多的独特“物种”。这些独特的思想家,更像是某种善于夜行的猫头鹰,就像黑格尔[25]在《法哲学原理》中的一句话:每当黄昏降临,密涅瓦的猫头鹰开始起飞。
智慧的猫头鹰们,读他们的书,不能指望从中得到“刀枪剑戟”那样的实用兵器,而是需要花些力气解读,要超越字面含义,并将其置于更大的历史背景中去审视。如果只停留在字面上,这些文本中的某些内容看着就像宏大的宣言了。尤其是第六章和第七章,那种内心的挣扎、向往、无奈和信仰交织在一起,如深海波澜。
温伯格的《混沌》这本书,字里行间流露出很多深度的思考,这是当下产业界冲锋陷阵的企业家需要静耳聆听的思想。
当然,这本书对“预测”的观点和立场也不是没有值得商榷之处:作者将可预测性转换到可解释性,进而又放弃可解释性,追求多重可能性和意义,这条思想进路是典型的西方文脉。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一是作者所指的“可解释性”诉求,是他所定义的“建立在概念模型”之上,扎根于牛顿图景的确定性世界的“可解释性”。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复杂性科学的历程印证了这一点,但“可解释”的含义也在深化。“可解释”遂与“可理解”两个概念靠得更近了,以至胡泳[26]老师一针见血地提出“相信机器,还是相信人?”这个终极拷问。也就是说,关于“可解释”诉求,并不是简单地“丢弃”“淡化”就可以释然的。
二是关于进化(进步)的方向。作者提出的“意义”问题,是一个好问题,也是过去至少50年来不同领域的思想者共同聚焦的问题。意义的生产过程、涌现过程如何,其弥漫、撒播过程如何,其塑造人性的过程如何,作者都没有给予太多的深究,反倒诉诸有点儿像基督精神那样的信仰,从“对人的重要性”的角度,最终归结为“新悖论”、敬畏等等,这就留下了太多空白。
自然,阅读即对话。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需要少数头脑从不同凡俗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来与我们的内心世界对话。精读这本书的价值,一方面在于理解作者的思想脉络,另一方面也需要关照当下异质文化碰撞中产生的文化间性,否则就只能是高声喝彩之后,别无他语了。

在智能技术日益陷入“解释和理解”的困境之时,对智能技术发展的方向就越需要加以警惕。二十年前美国政府关于聚合科技NBIC(Nanotechnology、Biotechnology、Information Technology、Cognitive Science)的报告[27]中,对聚合科技如何改变未来有这样一个判断:NBIC将会改变人类未来的物种。从西方文脉的演进历程看,他们对“改变物种”这件事情从来都没有心理障碍,从普罗提诺到奥古斯丁,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一众科学家、企业家和政治家似乎都没有心理障碍,这恰恰是一个非常值得忧虑的大问题。
过去10年来,很多人总是在不同场合爱引用这样一句话:未来已来。以此来表达对飞速变化的数字世界的感叹。然而,必须要问的是,这是谁的未来?如何决定现在?
这个大忧虑其实才刚刚开始。元宇宙作为时下流行的一个语汇,很好地聚合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虚拟现实等新兴智能科技,它将为世界剧变注入何种巨大能量?世界的意义和生命的意义,将会发生何种深刻的变化?这背后一系列基本问题值得深思。

比如说,符号学家乔治·莱考夫[28]关于“亲自性/具身性”的思想,我认为在今天智能技术渗透很深的境况下,值得进一步思考:人亲自做事情的空间,被大大挤压了,这意味着什么?很快,人们不需要亲自开车,不需要亲自烹饪,不需要亲自做家务,甚至不需要亲自阅读、不需要亲自工作(如果UBI的制度普遍化的话, 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普遍基本收入)。更加激进的想象是,更远的未来,我们可能不需要亲自吃饭,甚至可能不需要亲自交配繁衍后代。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景象,皆源于“亲自性”的大幅度削减。如果这种情况势不可挡地发生,那么一开始我说的“大忧虑”才刚刚开始。我们以为我们在继续人类驯服自然的史诗般的演化历程,以为是在驯服命运,像贝多芬那样扼住命运的喉咙——真实发生的,可能反倒是被某种命运紧紧的扼住了喉咙。

[1]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年7月13日—公元前44年3月15日),史称凯撒大帝,罗马共和国(今地中海沿岸等地区)末期杰出的军事统帅、政治家,并且以其优越的才能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奠基者。
[2] 朱嘉明(1950年- ),经济学家,横琴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任,苇草智酷创始合伙人。代表著作有《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未来决定现在》《元宇宙与数字经济》等。
[3] 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年3月6日—1564年2月18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绘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和诗人,文艺复兴时期雕塑艺术最高峰的代表,与拉斐尔和达芬奇并称为文艺复兴三杰。代表作有《大卫》《创世纪》等。
[4] 存在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18世纪欧洲神学的概念,是自上而下万物的分级。在“存在巨链”中,上帝居首,其下有九个等级的天使,天使之下是人类,其下为动物、植物、矿物。这一观念源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和普罗克洛斯等人的思想。
[5] 普罗提诺(Plotinus,公元205年—270年),又译作柏罗丁、普洛丁,古罗马时期的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创始人。有遗著54卷,由学生玻尔菲利辑为6集,每集9章,故称《九章集》。
[6] 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354年11月13日-430年8月28日),罗马帝国末期北非柏柏尔人,重要的天主教神学家、哲学家,主要作品包括《上帝之城》《忏悔录》等。
[7]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年7月28日—1994年9月17日),英国哲学家,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代表著作有《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年)、《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1963年)等。
[8] 王飞跃(1961年— ),智能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9] 人工社会、计算实验、平行系统——关于复杂社会经济系统计算研究的讨论,王飞跃,《复杂系统于复杂性科学》第1卷第4期,2004年10月
[10]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代表著作有《疯癫与文明》《性史》《规训与惩罚》《临床医学的诞生》《知识考古学》《词与物》等。
[11] 阿兰·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1912年6月23日-1954年6月7日),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被称为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之父。代表著作有《论数字计算在决断难题中的应用》《机器能思考吗?》。
[12] 阿隆佐·邱奇(1903年6月14日-1995年8月11日),美国数学家,1936年发表可计算函数的第一份精确定义,对计算理论的系统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13] 戴维·多伊奇(David Deutsch),美国量子物理学家,在量子物理学方面的研究颇有影响力。荣获2018年度“墨子量子奖”和2021年艾萨克·牛顿奖。
[14] 理查德·菲利普·费曼(Richard Phillips Feynman,1918年5月11日—1988年2月15日),美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1965年,因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的成就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5] 约翰·阿奇博尔德·惠勒(John Archibald Wheeler,1911年7月9日—2008年4月13日),美国物理学家、物理学思想家和物理学教育家。
[16] 戴维·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1950 年),美国作家、技术专家和演说家,哈佛伯克曼互联网中心研究员。
[17]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年10月20日-1952年6月1日),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也是机能主义心理学和现代教育学的创始人之一。代表著作有《哲学之改造》《民主与教育》等。
[18] 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1976年- ),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青年怪才、全球瞩目的新锐历史学家。代表著作有《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
[19] 道克·希尔斯,《Linux杂志》资深编辑,Upside、Omni和《个人电脑》撰稿人。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称他为“美国最可敬的科技作家之一”。2005年,被谷歌(Google)和奥莱利(O’Reilly)联合授予开源奖(Open Source Award)的最佳通讯员(Best Communicator)奖项。2006年,成为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加州大学的圣芭芭拉信息科学和社会中心的成员。
[20]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年11月10日-1546年2月18日)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发起人、基督教新教的创立者、德国宗教改革家。
[21] 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1928年10月8日—2016年6月27日),著名未来学家,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家之一。代表著作有《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权力的转移》等未来三部曲。
[22]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1943年-),美国计算机科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兼执行总监,《连线》杂志的专栏作家。因为长期以来一直在倡导利用数字化技术促进社会生活的转型,被西方媒体推崇为电脑和传播科技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大师之一。
[23] 彼得·蒂尔(Peter Thiel,1964年- ),被誉为硅谷的天使,投资界的思想家。1996年创办了Thiel资产管理公司。曾在1998年创办PayPal并担任CEO,2002年将PayPal以15亿美元出售给eBay,把电子商务带向新纪元。
[24] 凯文·凯利(Kevin Kelly,1952年- ),《连线》(Wired)杂志创始主编。1984年,KK发起了第一届黑客大会(Hackers Conference)。代表著作有《失控》《科技想要什么》《必然》。他的文章还出现在《纽约时报》、《经济学人》、《时代》、《科学》等重量级媒体和杂志上。被看作是“网络文化”(Cyberculture)的发言人和观察者,也有人称之为“游侠”(maverick)。
[25]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年8月27日-1831年11月14日),德国哲学家。代表著作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科学全书纲要》《法哲学原理》。
[26] 胡泳,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苇草智酷创始合伙人、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的最有影响的启蒙者之一。代表著作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数字位移——重新思考数字化》等。
[27] Mihail C.Roco and William Sims Bainbridge eds., Converging Technologies for Improving Human Performance.Dordrecht/Boston/Lond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此报告已由蔡曙山等人译成中文《聚合四大科技提高人类能力》,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28] 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认知语言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圣塔菲研究所科学委员会委员,国际认知语言学协会主席,认知科学学会理事会成员。代表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文章探讨了元宇宙作为数字时代新宠引发的思考,包括技术对人类感知、想象和秩序的影响。作者指出,元宇宙带来了感知的重塑、对高维空间想象的挑战以及新秩序构建的忧虑。同时,文章讨论了数学和算法在塑造世界模型中的作用,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提出了对确定性、解释性和未来发展的深度关切。
文章探讨了元宇宙作为数字时代新宠引发的思考,包括技术对人类感知、想象和秩序的影响。作者指出,元宇宙带来了感知的重塑、对高维空间想象的挑战以及新秩序构建的忧虑。同时,文章讨论了数学和算法在塑造世界模型中的作用,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提出了对确定性、解释性和未来发展的深度关切。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