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触摸的对称性:
普适计算时代的触感审思

文/ Ladewig,R., Schmidgen H.
《身体与社会》
Ladewig,R.,Schmidgen, H. (2022). Symmetries of Touch: Reconsidering Tactility in the Age of Ubiquitous Computing. Body & Society, 28(1-2), 3-23.
摘要
在当前技术与人体交互乃至嵌入人体的语境下,本文构建了一种“对称性”触摸理论。通过批判性地借鉴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对称性人类学”,将触觉能动性重新定义为“技术能动性”,将历来被认为仅属于人类特性的触觉概念拓展至非人行动者,并从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视角进行剖析。本文系统梳理了生物与技术的交融关系:从工业生产中的非人类触摸(如车床加工、印刷等),到19世纪生理实验室中对生物体的测量性触摸,再到现今媒介环境中无形的追踪、跟踪和传感。在强调数字现代性的触觉维度及其经济谱系时,本文旨在推进人和非人的触摸结合并重新审视普适计算时代的身体和技术。
**关键词:**环境媒介;传感器技术;触摸的对称性;触觉现代性
研究背景
现代社会与媒介设备交互的显著特点是触觉的回归,如打字、按压和滑动等触觉手势已成为与媒介设备交互的主要模式。然而,不仅是我们触碰媒介设备,媒介设备通过其传感、跟踪功能也在触摸和扫描我们。在这种Scoble和Israel预言的“场景时代”(Age of Context)或“触感时代”(Age of Contact)中,将人类经验转化为行为数据的主要前提,在于数字、移动和网络设备在促进消费、改善健康等过程中转向了人类身体。
行为数据被看作普适计算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新“黄金”(Zuboff,2019),在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作用中,生物体的数据有助于新的资本主义生物治理(bio-governance)形式和生物公民身份(bio-citizenship)的建立(Crandall,2010;Happe等,2018; Rouvroy,2012)。其中,生物和技术重新配置的关键条件,是当今现实世界技术环境向计算架构的不断转变,即以“计算融入环境”为总体趋势的21世纪媒介技术(Hayles,2009)。然而,此前在德国哲学家汉斯·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定义的技术世界中,“接触”被简单地视为“空间距离和空间本身的废除”(Anders,1970)。现今媒介技术已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态,不再需要笛卡尔意义上的物理“触碰”,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超越或颠覆人类与机器、生物与技术之间区别的配置,为重新审视所有生命体(无论是人类、动物还是植物)与其各自环境之间联系与边界的本体论提供基础。
主要内容
触觉反思
Parisi(2018)在《触摸考古学》(Archaeologies of Touch)中追溯了人机交互中触觉发展的技术科学研究历史,并主张“触觉现代性”。人类的主体性被卷入由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技术所组成的复杂系统中,成为一种“由技术元素、具身感觉和文化实践组成的不断变化的组合”(Parisi,2011)。本文在此基础上受到布鲁诺·拉图尔(Latour,1993)的“对称性人类学”启发,提出一种“对称性”触摸理论,受其人与物同等重要观点的影响,我们不再将触觉局限于“人类行动者”,而是赋予“非人类行动者”以触觉能动性,即触摸不再是人类独有的能力,而是被普适计算时代的传感器、扫描仪、跟踪器和类似设备接管和执行的操作。
然而,“对称性”并不意味着“同一性”,现今的媒体设备仍以与人类不同的方式接触其对应物,人类的触觉仍受限于“笛卡尔式的”常规物质或身体观念。一方面,国家对相关数据的追踪有其经济与政治利益诉求;另一方面,个体主体或整个群体接触媒介的表面动机却存在差异。不过,这样的差异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媒介正在触摸我们的事实。那么,我们该如何超越一般意义上的触觉,去反思这种“非人类触摸”呢?
技术触摸和折叠
非人类触摸与世界的一个总体特征相关,其在当代哲学中被称为“折叠”。吉尔·德勒兹将“弯曲”或“曲率”现象视为一种“纯粹事件”(pure event)(Deleuze,1993),而米歇尔·塞尔则认为身体的自触是意识的最终来源(Serres,2008)。在此基础上,让-吕克·南希认为触觉广泛存在:“我们的世界自我触摸,它会弯曲、变形并映射自身,并以这种方式自我影响并异己影响;它自我折叠,在自身内部产生作用,并顺从于自身。”在某种意义上,媒介技术的触觉能动性可被理解为世界普遍折叠的一个子集。我们希望具体了解媒介和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折叠”,实际上,任何通过工具媒介与物质进行的交互都可视为非人类触摸。印刷机历史就是技术触摸的历史,坚硬的印版用于触摸不同的较软材料,例如将黑色油墨印制到白色纸张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本雅明受包豪斯媒介触觉美学的启发,对机械印刷保持关注(Schöttker,1999),认为“早在文字可以通过印刷品复制之前,木刻图形艺术就变得可复制”(Benjamin,2007)。自19世纪初以来,可互换工具或机器零件(例如,手表的单个零件或步枪的单个部件)的工业生产都是通过压铸和冲压进行的。
科学领域出现的非人类触摸也逐渐扩展到人体。从19世纪中叶开始,仪器被系统地用于扫描和追踪“生命本身”,即动物和人的生物体。1847年,德国生理学家卡尔·路德维希首次使用记纹器(kymograph)记录动物血压的波动。1854年,德国医生卡尔·菲洛特开发血压计,以曲线的形式记录人类脉搏。1900年左右,生理实验室通过各种便携式记录仪器系统地收集生物体的运动和行为数据,并以表格、曲线和图表的形式呈现:从步态、个体手势、具体嘴和手的动作到运动练习、工具使用以及乐器演奏等(Brain,2015;Rabinbach,1990)。不过,现今的数字跟踪器不再需要这种笛卡尔式的触摸。Apple Watch使用“光体积变化描记图法”(photo plethysmograph,PPG)记录佩戴者的心率。步行者的动作不再需要像Marey那样通过充气鞋来记录,而是可以通过GPS信号进行无线追踪。只要有足够“大”的数据,就能创建相应用户的“数字足迹”。
身体与技术
在技治主义(technocracy)的影响下,各种动作被分解为时间片段,以便捕捉、展示并随后优化和标准化,特别是使用工具的动作,从较为简单的砌砖任务到复杂精细的手术器械操作。运动精确测量所产生的“度量标准化”,让人联想到“全景监狱”(panopticon)的形象(Gainty, 2012)。鉴于其旨在塑造“规训的身体”,这些过程显然可归入纪律规训的传统中(Foucault,1977)。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描述了一台用于纠正少年行为的机器,它能自动鞭打未成年人的身体(Foucault,1977)。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无数精巧装置和器械用非人类触摸取代了人类触摸来实施各种惩罚。
手势动作在人类学中被视为承载文化意义的载体。在马塞尔·莫斯的研究中,手势构成“身体技术”的核心(Mauss, 1973)。他关注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性的身体实践及其相应的身体手势,并指出“身体是人第一个也是最自然的工具,或者更确切地说,不讲工具,人的第一个也是最自然的技术对象,同时也是技术手段,就是他的身体”(Mauss,1973)。尽管莫斯的研究聚焦于探讨文化如何在身体和物质层面被“铭刻”,但他的几位学生继承并深化了他的研究。Hertz讨论了原始宗教信仰如何体现于(女性)手部使用的深层痕迹(Hertz,1909);Haudricourt没有采用吉尔布雷斯夫妇的手势动作解剖法,而是通过观察手势与工具的相互关系,强调在手部、工具及其作用对象间“接触形式”的重要意义(Haudricourt,1964)。
触觉无意识
本雅明在20世纪30年代探讨了现代性的“触觉体验”,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和《拱廊计划》中,指出技术会导致“切换、插入、按压”等手势的增长(Benjamin,2007)。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电视则是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能力的延伸(McLuhan,1994: 17)。瓜塔里和德勒兹将“触觉”与“视觉”结合并对比,将二者的具体关系与社会空间形式变化联系起来:一边是游牧者的平滑空间(smooth space),另一边是定居社会(sedentary societies)的条纹空间(striated space)(Deleuze &Guattari,1988)。同时,媒介理论者也没有将触觉分析局限于人类的能力和活动,报纸广告、广告牌,以及电影的动态影像积极地“迎向”(entgegenkommen)观众,而人眼只能像“减震器”一样对此反应(Benjamin, 2007),媒介在此过程似乎获得一种触觉能动性。参考本雅明(2007)提出的“视觉无意识”(the optical unconscious)概念,本文提出“触觉无意识”(the haptic unconscious)。
《拱廊计划》反映出20世纪初期在研究触觉方面发生的变化。19世纪的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主要将触觉视为人体的一种被动属性;在20世纪20年代,卡茨指出触觉作为一种近距离感觉,表现为“将主观的身体成分与物体的特性相结合”(Katz,1925)。触觉不仅位于可触摸或触摸中的人体维度,还应当转移到外界物体反过来作用于摸索的指尖以及抚摸或抓握的手感。正如梅洛-庞蒂认为触觉的独特之处在于“可逆性”(reversibility),即每一个触碰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接收触碰或被触碰的行为(Puig de la Bellacasa, 2009)。朱迪思·巴特勒则指出触觉在梅洛-庞蒂研究中并不仅是“单一的触碰行为”,更是“使得一个实体得以存在的假设条件”(Butler, 2006)。和本雅明和卡茨一样,麦克卢汉也强调媒介的触觉能动性,如电视图像是由“扫描描绘并不断成形的轮廓”(McLuhan, 1994)。
资本主义拱廊
瓜塔里在其关于艺术的著作中多次描述了个体媒介(如摄影、电影和绘画)作为二维设备的情境,它们首先吸引观众,然后捕获并紧紧抓住观众,仿佛在“呼唤他”、“拉扯他”,之后像吸盘一样牢牢地“粘附”在其表面(Guattari,2013)。在题出万物“拟有灵”(quasi-animist)的观点时,瓜塔里引用罗兰·巴特在摄影中提出的“刺点”(punctum)概念,认为元素可从摄影表面“射出”并“刺穿”观察者(Barthes, 1996)。因此,不仅是眼睛在扫描和触摸图像,图像也在扫描和触摸它的观察者。
现实论据支持我们将传感器社会的理解与本雅明、瓜塔里所描述的万物有灵论(animism)相联系。产业工人、艺术家、电影演员等被转变为商品之物,而商品则变成先验感性(transcendental-sensuous)的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Marx,1887)。报纸读者变为报道者,路人变成电影演员,电影中的演员却被贬低为道具,而道具却被视为真实的表演者,技术触摸和媒介的触觉能动性恰好无缝融入幻景(phantasmagoria)。对触觉能动性的重新审思需实现“对称性”。人的身体和媒介不再被视为相对静态和明确界定的实体,在普适计算时代,媒介已成为动态的主体,并不断重新定义着人-机边界。
AI大模型学习福利
作为一名热心肠的互联网老兵,我决定把宝贵的AI知识分享给大家。 至于能学习到多少就看你的学习毅力和能力了 。我已将重要的AI大模型资料包括AI大模型入门学习思维导图、精品AI大模型学习书籍手册、视频教程、实战学习等录播视频免费分享出来。
因篇幅有限,仅展示部分资料,需要点击下方链接即可前往获取
2024最新版CSDN大礼包:《AGI大模型学习资源包》免费分享
一、全套AGI大模型学习路线
AI大模型时代的学习之旅:从基础到前沿,掌握人工智能的核心技能!

因篇幅有限,仅展示部分资料,需要点击下方链接即可前往获取
2024最新版CSDN大礼包:《AGI大模型学习资源包》免费分享
二、640套AI大模型报告合集
这套包含640份报告的合集,涵盖了AI大模型的理论研究、技术实现、行业应用等多个方面。无论您是科研人员、工程师,还是对AI大模型感兴趣的爱好者,这套报告合集都将为您提供宝贵的信息和启示。

因篇幅有限,仅展示部分资料,需要点击下方链接即可前往获取
2024最新版CSDN大礼包:《AGI大模型学习资源包》免费分享
三、AI大模型经典PDF籍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AI大模型已经成为了当今科技领域的一大热点。这些大型预训练模型,如GPT-3、BERT、XLNet等,以其强大的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正在改变我们对人工智能的认识。 那以下这些PDF籍就是非常不错的学习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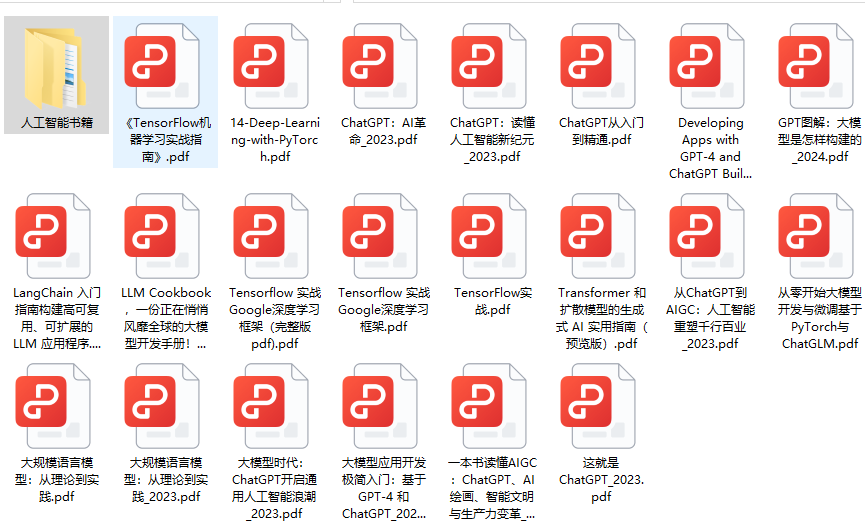
因篇幅有限,仅展示部分资料,需要点击下方链接即可前往获取
2024最新版CSDN大礼包:《AGI大模型学习资源包》免费分享
四、AI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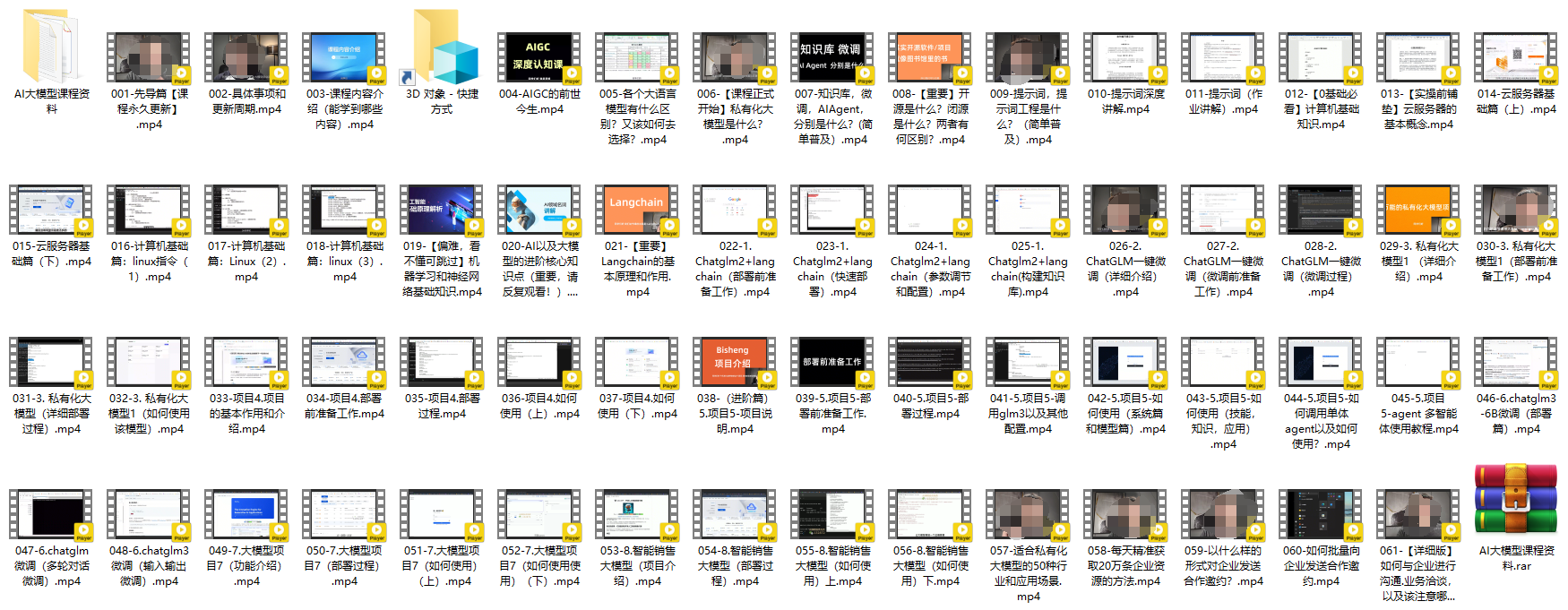
因篇幅有限,仅展示部分资料,需要点击下方链接即可前往获取
2024最新版CSDN大礼包:《AGI大模型学习资源包》免费分享
作为普通人,入局大模型时代需要持续学习和实践,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和认知水平,同时也需要有责任感和伦理意识,为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