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言学、考古学与希腊人种族起源研究
徐晓旭
提要:希腊人的种族起源是一个技术难度大且极具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问题。正是历史语言学和考古学,而非相信起源神话包含历史真实性的历史实证主义史学,对该问题的研究发挥了实质性的奠基作用。并且,在历史语言学和考古学主导下的多学科交叉合作、多种方法和理论模式的综合运用,使得人们对原始印欧人及其语言和故乡、前希腊底层语言、“希腊人的到来”等史前历史的认识日益走向深入。这项研究的一系列的成功可以为史前史、古代史乃至新兴的全球史若干领域提供诸多技术、路径和视野上的经验参照。
关键词:历史语言学;考古学;原始印欧人;前希腊底层;原始希腊人
希腊人的种族起源是希腊史、古代史和史前史领域内一个重要且具有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问题。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它是观察希腊史的起点。其理论和方法论意义则在于它是一个难题,一宗难破的史前疑案。调查其“案情”,需要取用和甄别传统文献、语言、文字、考古、基因等各类证据,要采用古典学、历史学、历史语言学、考古学、古文字学、遗传学等学科的多种方法和路径。其研究当中发展出的诸多有效的理论和模式,无疑又可以为古代史和史前史领域其他起源及类似问题的研究提供经验、样板以及理路的多种可能参照。
本文旨在提供一份关于希腊人种族起源问题研究史的理论性观察和解析,但重点展现的是历史语言学和考古学在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原因是这两个学科提供的证据和研究路径为该项研究奠定了可行且可靠的基础,关于希腊人起源的各种理论也都是由这两个学科提出和发展的。相比之下,相信神话传说具有历史性的“历史实证主义”(historical positivism)方法,在严格的史料批判面前,在考古发现、历史语言学证据、新的人类学理论和古遗传学研究成果的检验之下,已被证明无效,因此本文只对其方法论缺陷做一简要评析。近些年来,古遗传学替代了以往的体质人类学,成为人类种群历史研究的新手段,产生了一大批关于欧洲人血缘和印欧人起源的研究成果。但基因证据的分析依然离不开以历史语言学、考古学和主要建立在两者基础上的史前史研究已获得的各种认识作为参照系。只有同这些认识进行比对,实验结果才可能获得更为合理的解释。基因研究的目标和结论也通常表现为证实、否定或修正这些认识。由于这一点,同时也考虑到本文的关注重心及篇幅限制,笔者仅在相关场合对希腊人种族起源以及与之最为相关的古遗传学研究结论做顺带的简介。
一、神话传说与历史
古代希腊人关于自身起源流传最广的传说是:希腊大陆最初为皮拉斯基人等众多族群所占据,希腊人只是其中一个小族群,后来不断扩展并同化其他族群,最终发展成一个遍及希腊的大族群。希腊人(Hellenes,单数Hellen)及其各大支系的得名始祖是希伦(Hellen)及其子孙。相信神话传说保存了所谓真实的历史内核的人会以此为据,并经常会将考古、人种和语言等证据与之对应加以解释,重构一部希腊种族在前希腊人占主体的大陆扩张的史前史。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盛行这种把神话传说直接当作历史对待的历史实证主义。
今天历史实证主义已成明日黄花。我们不妨从霍尔对它的批判中看一下其方法论缺陷。霍尔指出,历史实证主义学派将族群起源神话看成对晚期青铜时代末人口迁移的模糊曲折的记忆,把这些神话有时相互矛盾的异文视为对某种“真实的”历史记忆的病态偏离,即由于时间流逝而造成的一种集体失忆,甚或歧忆;历史实证主义者的任务是把这些相互矛盾的异文调和到一个单一的、合理化的综合解释当中,以揭示“实际发生了什么”。对此霍尔以人类学为依托批评道:“族性不是一种原生的既定事实,而是通过话语策略被重复地和主动地建构的。”“族群起源神话显然正是这些策略运作时所凭借的媒介之一。其功能是界定和主动建构群体身份认同,乃至于只要是群体关系变化了,谱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能让我们追溯这种谱系改动的东西,恰恰就是神话异文的出现,即偶然幸存下来的较早因素与更晚因素并存,但并不协调。这样,我们就不应该把神话异文看作集体记忆衰退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应看到它们标示了族性话语建构中的特定阶段。存在于这些异文之间的矛盾或‘断裂点’可以用于廓清族群起源神话被编造、重组和改造时所用的各个建筑砌块”。另外,正如我们后面看到的,也有新发现的基因证据否定神话传说和以之为基础的历史实证主义结论的实例。
事实上,甚至在历史实证主义盛行的时代,都不乏对神话传说的史料批判者。迪勒就是这样一位。他指出,古代希腊大部分起源神话都是后荷马时代人为编造的产物,代表希腊人的希伦家族谱系神话更为晚出,促使更早存在的其他名祖谱系被当时人归为非希腊和前希腊的族群所有。正因如此,今天在讨论希腊人生物学意义上的起源时,希腊古典文献中保留的名祖神话和起源传说是需要排除的,它们作为史料的合理使用场合应该是关于历史时期以“希腊人”为族称的族群及其次族群的身份认同的研究领域。
与此相关,还须澄清一个族称使用问题。“希腊人”在荷马史诗中还不是说希腊语的人口的总称。它发展成全体意义的族称以及围绕它形成新的族群身份认同,是后荷马时代的事情。可是对这些自称为“希腊人”的人群之前的与之说同一种语言并构成其生物学祖先的人口,我们不也称为“希腊人”吗?其实,从人类学视角来看,希腊人的自称和身份认同表述是一种“主位观”(emic),即当事人视角;我们对他们的称呼和描述则属“客位观”(etic),即研究者的观察和认知。为了方便,我们采用“客位观”把尚未自称为“希腊人”的说希腊语的人口也称为“希腊人”。历史实证主义学派却混淆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主体。
不过,历史语言学研究的确显示,说希腊语的人口是更晚到达希腊的移民,此前的居民因而被学者称为“前希腊人”。这岂不也证实了起源神话的历史性?!然而这不过是一种由巧合带来的幻象:两者仅在各自所言的“前希腊人”和“希腊人”的前后次序或者说相对年代上达成了偶合。深究其各自绝对年代,便不难发现两者揭示了两段不同的历史:历史语言学要研究的“希腊人”和所推定的“前希腊人”属于史前时代;希腊的历史时期开始于公元前8世纪后半期荷马史诗被用字母记录下来,起源神话大多是后荷马时代出现的,作为希腊人名祖的希伦及其子孙的神话最早于公元前6世纪才见诸一部诗作。由此来看,是在荷马之后的某一时期,所有说希腊语的人口才最终选择将“希腊人”作为自己的共同族称,具有相应身份认同的族群意义上的希腊人也才得以形成。而希伦及其家族的谱系神话、希腊人同化前希腊人的传说,正是希腊人建构自身认同的一种历史投射式的话语表述。
二、原始希腊人与原始印欧人
正如历史实证主义者时常会求助历史语言学证据一样,一位历史语言学家有时也免不了受神话传说的影响。不过,相较历史实证主义对史前史研究的损伤而言,历史语言学对神话传说基本上是免疫的。这是因为历史语言学对其研究对象——语言,实施一种孤立封闭的对策,即仅从分析语言本身来推断语言及其使用者的历史,从而能够最终排除文本叙事的干扰。历史语言学最常用的方法是对不同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进行比较,以发现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系统的相似性或对应关系。比较研究不仅证实了希腊语属于印欧语系,还发现了希腊语中包含数量不菲的前希腊底层语言成分。前一项研究结果暗示了希腊语及其持有者即学者所谓的“原始希腊人”起源于希腊之外,后一项则意味着“前希腊人”是希腊更早的居民。
1786年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爵士指出,梵语与希腊语、拉丁语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上具有“不可能是偶然产生的相似性”,因而应“来自某个共同的源头”,他还推测哥特语、凯尔特语和古波斯语也与之有共同起源。人们通常将此视为“印欧语系”被“发现”的标志。尽管有学者认为琼斯“发现”的重要性被夸大了,但的确紧随其后,历史比较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兴起了。19世纪的语言学家运用系统的比较方法,证实了印欧各语言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的同源关系。印欧学家们的探索热情一直持续至今。
被划归印欧语系的语言大约有140种,它们又被大致划分为凯尔特语族、意大利语族、日耳曼语族、波罗的语族、斯拉夫语族、阿尔巴尼亚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弗吕吉亚语、安纳托利亚语族、印度-伊朗语族和吐火罗语12个主要的语族或语言以及一些孤立的语言。各语族(或语言)之间关系远近并不相同。希腊语与亚美尼亚语通常被认为关系最亲密,两者或拥有共同祖先,或在分化成独立的语言之前有过密切的接触。希腊语与印度-伊朗语族也具有较近的相似性,但其间关系不及与亚美尼亚语紧密。希腊语与相邻的弗吕吉亚语和马其顿语(如果它不构成希腊语一种方言的话)也被认为存有强烈的相似性,但这两种语言语料较少,不允许人们对其关系做进一步判断。
围绕原始希腊人和原始印欧人的诸多问题,目前并未最终获解:各印欧语言扩散到欧亚广大地区之前,其祖语(parent language),即原始印欧语是在哪里被说的?原始印欧人的故乡(Urheimat)在哪里?原始希腊语的前身是何时从原始印欧语中独立出来的?原始希腊人何时迁入希腊?学者采用多种研究手段,提出了各种理论,但至今仍未得到一致信服的答案。
在关于印欧人故乡的诸种假说当中,由立陶宛学者玛利娅·金布塔斯女士最先系统阐述的“库尔干假说”被认为与重构的原始印欧语所反映的原始印欧人的文化特征最为接近,从而在印欧学者中获得了最广泛的接受,“库尔干文化”也经常被用作原始印欧人的同义语。它是黑海-伏尔加地区的一系列铜器和青铜时代文化的总称。金布塔斯将其特点归纳为:季节性定居、半地穴式住宅、畜牧业经济、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强有力的家长制的家族制度、尚武好战、小屋式墓室的巨坟(俄语kurgan“库尔干”即“巨坟”)、动物用牲、马的使用与崇拜、太阳神崇拜。在她看来,这种文化与“旧欧洲”文化,即库尔干部落侵入前的欧洲新石器和铜器时代各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后者的特点是:居民是在大村落或城镇中过着和平定居生活的农民;社会为平等的母系制;女性神崇拜受到特别的重视。金布塔斯提出,公元前4500—前2500年,库尔干文化从它在乌克兰和南俄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区的故乡向亚洲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区西部、高加索地区、东南欧和中欧扩张。向欧洲扩张有三次大的浪潮,分别发生在约公元前4500—前4300年、约公元前3500年和约公元前3100—前2900年。在第三次扩张浪潮期间,原始希腊人的前身正在即将到达希腊的途中。属于此次扩张的代表文化之一的亚姆纳(乌克兰语Yamna,俄语Yamnaya)文化从黑海-里海一带的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区向多瑙河流域和东巴尔干扩展,散布于巴尔干的几千座“库尔干”巨坟一直向南扩散至阿尔巴尼亚和北希腊。金布塔斯把希腊境内发生于早期希腊底II和III之间的文化变化归因于说印欧语言的库尔干人口到达了希腊。“库尔干理论”所受的质疑主要在于考古资料的解释方面。库尔干文化的某些所谓“特征”在库尔干扩张之前的一些欧洲文化中也有发现。尽管如此,第三次扩张浪潮是得到了最好证实的一次,亚姆纳文化为之提供了重要证据。
另一种与之竞争并颇具影响力的理论是剑桥大学考古学家科林·伦弗鲁提出的“安纳托利亚假说”。伦弗鲁把印欧人的故乡放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及其以东和以南的邻近地区,把原始印欧人共同体存在的时间确定在约公元前6000年以前。他将印欧人的扩散同新石器时代初期农业经济的传播联系起来,认为传播农业的正是说印欧语的人口。这种理论最主要的缺陷恐怕有二。一是它主张的年代过早,超过了原始印欧人共同体存在的时间深度,同源词所指示的犁、羊毛、轮车、马等印欧文化特征在公元前6000年之前尚未出现。二是它所描述的印欧语言扩散模式与印欧语言的实际分布格局不相兼容。按照该理论的逻辑,农业是呈波状从西亚向外扩散的,那么随之传播的印欧各语族、语言也得呈现出亲缘关系与地理分布成正比的循序渐进格局。但在实际的语言地理当中,各印欧语族、语言却表现出逆序和离散的分布状态。例如,希腊语与亚美尼亚语、印度-伊朗语族关系最近,按此假说,三者应在地理上相连,但在实际当中,希腊语与后两者为安纳托利亚语族乃至非印欧语言所隔离,而安纳托利亚语族和与之关系较近的意大利-凯尔特语族之间又有希腊语和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印欧语言插入。这种语言分布格局的形成显然无法用农业从安纳托利亚向外波状扩散来解释。
最近些年遗传学领域发展出了从古人类遗骨中提取DNA检测的技术,这比之前单纯依靠研究现今人群基因更能准确地重构人类的演进、分化、迁徙、融合和分布等复杂的种群历史。在印欧人起源问题上,最新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古样本以及古样本与现今人群基因比对基础上的,其结论大多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支持“大草原假说”,即“库尔干假说”。拉扎里迪斯及其同事提出,至少有三个人群对今天欧洲人的血缘有贡献:一是古欧亚北部人群,他们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西伯利亚人有着最近的亲缘关系;二是西欧狩猎采集者;三是来源于近东的早期欧洲农民。琼斯等研究者又发现,高加索狩猎采集者构成欧洲人的第四个祖源。不过,“古欧亚北部人群”仍是一个推想出来的人群,被归于他们的基因连同高加索狩猎采集者的基因被研究者认为主要是由亚姆纳文化人群直接带入的。亚姆纳文化人群拥有混合祖源。一部分祖先来自东欧狩猎采集者,他们与2.4万年前的西伯利亚人群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另一部分祖先来自一支近东人群,在基因构成上很像今天的亚美尼亚人,很可能属高加索狩猎采集者;或者是一支来自伊朗西部的铜石并用时代人群,该人群由伊朗西部和利凡特的新石器时代人口与高加索狩猎采集者混合而成。更直接地说,现代欧洲人就是西欧狩猎采集者、欧洲早期农民和亚姆纳牧人三个古代人群的混血。他们当中常见的Y染色体单倍型类群R1a和R1b便是由亚姆纳牧人携带而来。哈克等人指出,中欧的绳纹陶文化人口有大约75%的血缘可追溯至亚姆纳人,这证明了一场由欧洲东部边缘向欧洲腹地进发的大规模移民。阿伦托夫特等人也宣布,他们提供的基因组证据证实了来自黑海-里海草原的亚姆纳人群向欧洲北半部和中亚的扩展,这与推测的印欧语言的扩张相一致。
相比于中、西和北欧人群拥有高比例的亚姆纳血缘,南欧地中海居民的基因构成似乎并未受到大草原移民的深度改变。这也被萨尔诺等研究者理解为亚姆纳文化并非所有印欧语言支系的来源,巴尔干和地中海沿岸各人群内少量亚姆纳文化的基因只是更晚才进入的,他们拥有的与高加索及利凡特人群相关联的血缘意味着一次更早的单独移民事件,印欧语言在这些地区的出现可能与此次移民有关。休吉等人则证明了克里特青铜时代的米诺斯人与新石器时代居民和现代欧洲人有着密切的遗传关系,并将其祖源追溯至安纳托利亚农民。他们认同伦弗鲁的理论,即原始米诺斯语是大约9000年前由原始印欧语分化出的一个分支。
2017年公布的一项关于米诺斯人和迈锡尼人基因的研究又显示,亚姆纳文化人群的基因流入了希腊。拉扎里迪斯等研究者发现,克里特的米诺斯人和希腊大陆的迈锡尼人在基因上是相似的。两者至少有3/4的血缘来自“本地”祖先,即西安纳托利亚和爱琴海新石器时代的第一批农民。其余血缘大部分来自“东方”祖先,他们与高加索和伊朗古人群有亲缘关系。这部分“东方”血统以前被包括拉扎里迪斯本人在内的研究者解释为青铜时代来自欧亚草原的牧人带入欧洲的,他们是东欧狩猎采集者和来自高加索和伊朗的人群的混血。此次研究发现,“东方”祖先也可以是自己独立到达的,至少对于米诺斯人如此,他们身上没有东欧狩猎采集者的血缘。与米诺斯人不同,迈锡尼人还有另外一群“北方”祖先。迈锡尼人4%—16%的血缘最终与东欧和西伯利亚的狩猎采集者相关联。这种“北方”血统有它更近的直接来源,它可以解释为由与铜石并用时代到青铜时代亚美尼亚人群有亲缘关系的人群带入的,或者还可能是青铜时代来自大草原的移民引进的,两者都携带了东欧狩猎采集者的基因。
但研究者也指出,迈锡尼人的“北方”祖先的到来是属于对希腊的零星渗透,还是如同发生在中欧的那种快速移民,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如果是后者,那它将支持原始希腊人构成印欧人自大草原入侵的南翼的观点。然而,来自安纳托利亚的皮西狄亚(Pisidia)的青铜时代古人样本缺乏“北方”祖源,而那里已被证实古代存在印欧语言,这种情形又给基因和语言的关联投上了疑问。这就需要收集更多的古代安纳托利亚语族人群的样本来检测。
在历史时期的古代希腊人群样本缺乏的情况下,这项对米诺斯人和迈锡尼人样本展开的研究对于观察历史时期古代希腊人的血缘构成无疑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研究者也将古样本与现代希腊人样本进行了比对,发现现代希腊人与迈锡尼人的基因成分相似,但同迈锡尼人比起来,他们与新石器时代农民共有的等位基因更少,这显然是由于后来历史上发生的人口混入而使新石器时代的血缘受到一定程度的稀释所致。从这点来看,这项研究也证实了希腊大陆自接纳印欧移民和使用原始希腊语以来人群血统的延续性。此外,研究者并没有发现米诺斯人和迈锡尼人的祖源当中有来自埃及或利凡特的成分,从而否定了伯纳尔用其三大卷《黑色雅典娜》精心编织起来的青铜时代埃及和腓尼基殖民者征服希腊的理论。这也等于宣告了他以达那奥斯和卡德摩斯移民希腊的神话作为指引和证据的历史实证主义方法的失败。
三、希腊语中的前希腊语言底层
希腊语是原始印欧语的一个保守的代表。在印欧各语言中,其语音最为保守。它保留了原始印欧语中的全部元音(即长、短i,e,a,o,u)、原始印欧语的自由重音(动词重音除外)、不送气清塞音(* p,* t,* k)、不送气浊塞音(* b,* d,* g)和送气浊塞音(* bh ,* dh ,* gh,以送气清塞音ph ,th ,kh的形式出现)的对立。希腊语在形态上也同样表现出保守性。它保持了名词和动词的三个数(单数、双数和复数)、动词的三个体(现在体、不定过去体和完成体)和主动与中动和被动的区别、名词和形容词的五个格以及另外两个格的痕迹。没有证据表明希腊语的词法和句法曾受过非印欧底层的严重影响。但另一方面,从词汇上看,据估计希腊语有一半以上的词不能和其他印欧语言做同源词比较。一项对《新约》中《马太福音》2和《路加福音》15两章的印欧语言译本的词汇调查显示,非印欧及词源不明的词语数量在俄语译文中为15个,立陶宛语中为34个,意大利语中为48个,希腊语中则高达171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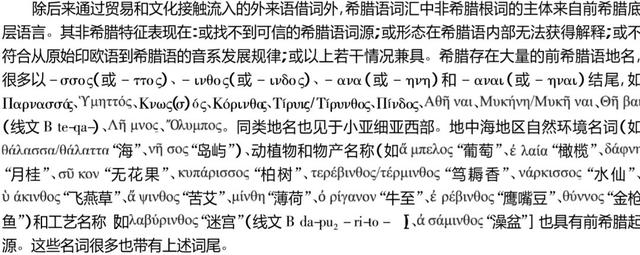
对于前希腊底层到底属于什么语言,学者意见大体可以分为两派,即“爱琴派”和“印欧派”。前一派通常将前希腊底层冠以“地中海语”或“爱琴海语”之称,认为它是一种遍及地中海,属于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的非印欧语言。其理由是希腊语中的前希腊词语很多都无法从印欧语角度进行分析,而一些也出现于地中海地区的其他语言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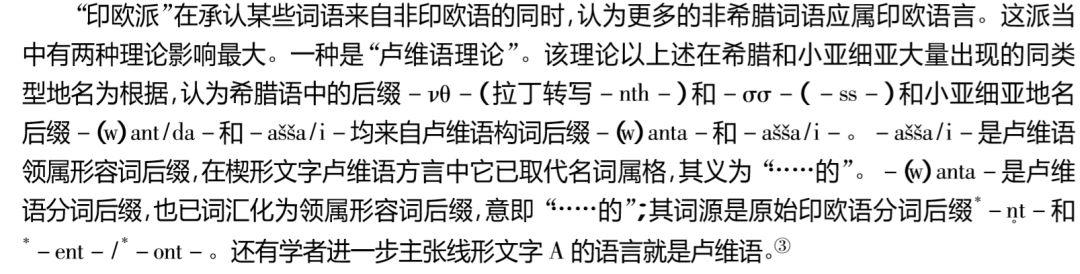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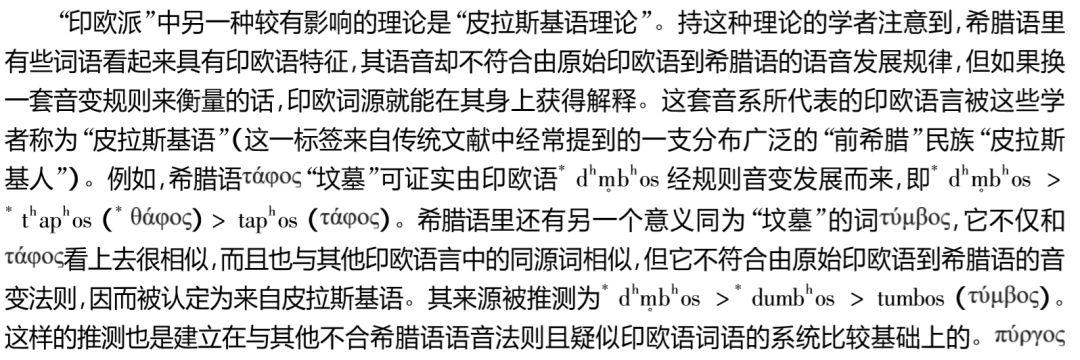

各理论都不乏看上去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也提示人们需要估计到希腊语中前希腊底层构成的可能的复杂性:非印欧因素和印欧因素也许都存在,而且在构词方面非印欧语言因素有些时候可能与前希腊的印欧底层或希腊语自身已整合在一起。希腊学者萨凯拉里欧就发展了这样一种复合式底层的理论:前希腊的希腊先后为“地中海”因素和印欧因素所占领;前希腊的印欧人有四支,即皮拉斯基人、(原始)阿凯亚人、海摩奈斯人和德吕奥佩斯人。
多种前希腊语言遗存也暗示了前希腊底层的复杂性。在希腊和爱琴海地区发现的各种文字中,迈锡尼线形文字B(约公元前1400—前1200年)已被文特里斯破译,其语言为希腊语;大多数塞浦路斯音节文字铭文也已被证实记录的是希腊语。其他文字虽未获破译,但其语言均表现出不属希腊语的特征,至少绝大部分应被视为前希腊语言的直接证据。米诺斯象形文字(公元前2100—前1450年)、“法伊斯托斯圆盘”铭文(公元前1800—前1600年)、“阿尔卡洛科里双头斧”铭文(公元前1600年)、线形文字A(公元前1750—前1450年)皆未被破译。对线形文字A记录何种语言不断有人给出答案:塞姆语、卢维语、赫梯语、卡里亚语、吕基亚语、胡里语等。由线形文字A直接或间接发展来的所谓“塞浦路斯-米诺斯文字”实际上包含了几种文字变体,它们也许被用于书写不同的语言。其各文本在年代上跨越
约公元前1600—前1050年。与之有谱系联系的塞浦路斯音节文字也具有两种变体。其铭文绝大部分书写的是希腊语塞浦路斯方言,少量记录的是一种尚未破译的语言,学者称之为“真正的塞浦路斯语”。塞浦路斯音节文字一直被使用到公元前3世纪,其最早的铭文(书写塞浦路斯方言)年代也许早到大约公元前11世纪。真正的塞浦路斯语铭文年代在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到公元前4世纪末。除与线形文字 A有亲缘关系的各种线形音节爱琴文字外,在克里特还发现了另一种用希腊字母拼写的非希腊语言铭文,该语言被学者称为“真正的克里特语”(名称来自传统文献中的“真正的克里特人”),也没被破译。
铭文年代约为公元前650年至公元前3世纪或公元前2世纪。莱姆诺斯岛出土的约公元前6世纪的墓碑铭文在字母和语言上与埃特鲁里亚语相似,人们普遍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在萨摩色雷斯发现的公元前6—前4世纪的70多件陶器等小物件铭文均用希腊字母书写,但又不是希腊语,有学者将之断定为色雷斯语。目前尚不能确定这两种语言是前希腊语言,还是在希腊人定居爱琴海地区之后由新移民带入的。
日益深入的古遗传学研究也会对观察前希腊人问题提供帮助。一系列古基因检测都证实了考古学所揭示的农业从近东向欧洲扩散是通过移民而非单纯的农业文化传播实现的,来自近东的早期农民构成了今日欧洲人的三大祖源之一,爱琴海和希腊恰是新石器时代农业和农业移民到达欧洲的第一站。考古显示农业是沿地中海和中欧两条路线传遍欧洲的。菲尔南德斯等人通过对古人样本基因的研究认为,最早是利凡特的农民沿安纳托利亚南岸,取道海路,经由塞浦路斯、克里特和爱琴海岛屿,前往希腊西海岸并殖民欧洲的。但这种认识为更新的研究所否定,拉扎里迪斯等人证实了新石器时代欧洲农民与安纳托利亚农民要比利凡特农民共享更多的等位基因。西北安纳托利亚和希腊新石器时代的农民目前被研究者认为是欧洲早期农民的祖源。因此,将前希腊底层语言推定为他们的语言也不无理由。在克里特和安纳托利亚高频出现的Y染色体单倍型类群J2a-M410人群被推测为说安纳托利亚语族的一种语言,米诺斯人的线形文字A被认为记录的就是这种语言;或者另一可能是他们说一种与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哈梯语有亲缘关系的非印欧语言。
米诺斯人和迈锡尼人的早期青铜时代与高加索人群有亲缘关系的“东方”祖先也可构成前希腊底层的选项,毕竟其到来更为晚近,且移民横扫地中海南欧。这次基因流入不仅与希腊大陆、克里特和安纳托利亚出现的大量非希腊语地名相关联,整个爱琴海地区早期青铜时代出现一种同质的考古学文化也很难说与这次移民无关。纵或可以令这次移民为印欧语言在巴尔干和地中海的出现负责,但这样解释会违背印欧各语族的关系原则:意大利语族和凯尔特语族关系最为密切,甚至经常被归为一个更大的语族,后者的基因已被证实由亚姆纳移民带入,前者的到来却被归因于此次“东方”移民!既然这批移民与高加索人群有基因上的联系,不妨可以将其语言往高加索语言或其亲属语言上推测。当然,高加索地区语言生态复杂,并存好几个语系的语言,胡里语是其一。索斯伯根即采用胡里语解读线形文字A。
四、希腊人的到来
人们对原始希腊人在何时由何地到达希腊也有意见分歧。既然重构的原始印欧语词汇反映的物质文化特征与考古资料对照所确定的原始印欧人共同体存在的时段为公元前4500—前2500年,那么“希腊人的到来”不应早于公元前2500年。这样,目前被讨论的可能年代主要有四个,依据是考古学地层中的四次文化中断或变化:早期希腊底II和III之间即约公元前2100年、早期希腊底和中期希腊底之间即约公元前1900年、中期希腊底和晚期希腊底之间即约公元前1600年、晚期希腊底IIIB和IIIC之间即约公元前1200年。被考虑的可能来自线路方向大致有二,即由北(巴尔干)或由东(爱琴海、安纳托利亚)。
持“约公元前1200年说”者最少。他们把希腊人到来的时间放在迈锡尼文明被毁的时刻,这也意味着他们要面临如何对待线形文字B的问题,这种属于迈锡尼文明的文字已获破译并被证实记录的是希腊语,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前1200年。
主张“约公元前1600年说”的学者各自的论证不甚相同,其中最常被使用的证据是迈锡尼“竖井墓”和马拉战车。“竖井墓”中的青铜武器、金、银、象牙、琥珀等贵重随葬品所反映的好战而富有的“竖井墓王朝”被他们视为由刚刚到达的希腊人入侵者所建,而非社会进步和革新的产物。一系列的考古资料,如“竖井墓”墓碑和随葬的金指环上描绘马拉战车的浮雕、墓中出土的马嚼子部件、线形文字B记载的马拉战车清单,都证实了马拉战车于大约公元前1600年在希腊首次出现。一些学者认为,希腊语中称呼马拉战车部件的名词具有印欧语词源这一情况意味着原始希腊人进入希腊之前就已知道使用战车,从马拉战车在希腊出现的时间来看,希腊人移入希腊不可能在大约公元前1600年之前。
“约公元前1900年说”曾是最广为接受的正统理论。20世纪初迈耶和贝洛赫等人通过对印欧语言分化及希腊语方言分化和当时已有考古资料的分析,将第一批希腊人到达的时间推测在公元前3000年代和公元前2000年代之交。1918年,魏斯和布里根又注意到,希腊大陆的“早期希腊底陶器”与同时期早期米诺斯和早期基克拉迪陶器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这表明希腊大陆和克里特岛、基克拉迪群岛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属于同种文化类型。到中期希腊底初,一种新型的灰色光滑的轮制陶器即“米尼亚式陶器”突然出现,几乎同时“早期希腊底陶器”消失,这种中断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类型的引进。晚期希腊底的迈锡尼文明则是克里特的米诺斯文明影响并吸纳本土中期希腊底文化的产物。在两人看来,弄清“米尼亚式陶器”所标志的中期希腊底文化对早期希腊底文化的取代以及后者的种族不可能被灭绝等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能够揭示“历史时期在希腊居住的人种的种族起源和亲缘”。
1928年,布里根又与哈雷合作发表了极具影响力的论文《希腊人的到来》。哈雷在前人菲克和克莱池默对于希腊语中前希腊语地名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绘制了一份希腊和爱琴海地区的前希腊语地名地图,并对这些地名的分布进行分析,进而推断其可能的来源。这些为数不菲的非希腊语地名表现出与小亚细亚的大量地名之间存在关联的特征:或完全等同,或具有共同的后缀[很多带有后缀-nth-或-s(s)-],或词根相同或相似,或前两种甚至三种情况兼具。小亚细亚西部的这类地名一直散布至相当远的内陆,有的甚至出现在中部腹地,均超出希腊人的影响范围。而且,小亚细亚的很多地名虽带有同类后缀,却并未出现在希腊或根本没有进入希腊语。这些情况表明,这类地名可能都是被从小亚细亚带到希腊的。
布里根更详细地分析了这些地名的分布,认为它们所指示的一个前希腊语言家族占据了克里特、基克拉迪群岛、伯罗奔尼撒南部和东部以及中希腊,其分支进一步向北、西北和西扩展至邻近地区,这也意味着一次由南向北的语言移民。接下来是要寻找一个考古遗存分布与这些地名分布相吻合的时期,因为断定了前希腊语所属的考古学地层,就可以认定最初的希腊人是在随后的地层上到达的。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爱琴海各地考古学文化特征,布里根将与前希腊语地名相一致的考古学年代断定在早期青铜时代。早期米诺斯、早期基克拉迪和早期希腊底文化构成一种同源文化的地域分支,而之前新石器时代、之后中期和晚期青铜时代克里特、基克拉迪群岛和希腊大陆的各考古学文化均不具备这一同质特征。克里特的中期米诺斯文化是由早期米诺斯文化毫无中断地发展而来,语言和种族都在延续;在希腊大陆,早期希腊底文化在遭受入侵中终结,入侵者带来了“米尼亚式陶器”,文化和种族都有很大改变;在中期基克拉迪的地层中则能看到“米尼亚式陶器”和来自克里特的“卡马瑞斯式陶器”同时流入。从中期到晚期希腊底,考古遗存表现的是文化的延续发展。这一切表明,早、中期希腊底之交带来“米尼亚式陶器”的入侵者就是第一批希腊人。
“约公元前2100年说”是目前最流行的观点。1952年凯斯齐在阿哥利斯的莱尔纳发掘,这座城镇也许是全希腊最重要的早期希腊底文化中心。发掘表明,约公元前3000—前2100年,莱尔纳存在一个具有较高发展程度的社会,其宏伟的建筑引人注目。但到约公元前2100年,莱尔纳被毁,随后的早期希腊底III相对贫穷。在被毁后的地层中,凯斯齐发现了一种早期形式的米尼亚陶器,即“原始米尼亚式陶器”。经调查得知,阿尔戈利斯、阿提卡,甚至南拉哥尼亚的其他一系列地点在早期希腊底II和III之间似乎也遭到破坏。虽然早期希腊底III的证据较为缺乏,但某些学者在重新检验后认为中期希腊底与早期希腊底III之间存在着连续性。这促使很多人把第一批希腊人迁入希腊的时间前推至约公元前2100年。
不过,最先发现早期希腊底II和III之间中断的凯斯齐却倾向于维护“约公元前1900年说”,从而提出了“两波说”,认为发生过两次入侵:约公元前1900年的入侵者是希腊人,约公元前2100年的入侵者可能同希腊人有亲缘关系。他试图将他们推测为鲁维人,但又对此存疑。萨凯拉里欧也持“两波说”。他以接受“库尔干假说”为前提,认为两次入侵者均为原始希腊人,且当中伴有巴尔干移民,第二次入侵的是原始希腊人的大部。他还将“达那奥伊人”[Dana(w)oi]断定为原始希腊人的族称,该称正是荷马称呼希腊人的族称之一。
综上来看,公元前2100/1900—前1600年这半个世纪的首尾是希腊人到来时间的最有可能的选项。“约公元前2100/1900年说”影响虽大,仍无法否定“约公元前1600年说”的某些理由,后者也难于说服每位公众。选择关键在于对迈锡尼文明的评估。线形文字B表明迈锡尼世界是一个使用希腊语的人口和文化共同体。如果希腊语是其唯一的语言,那么是否意味着原始希腊人同前希腊人的融合早已完成,原始希腊语也早已取代前希腊语言并吸纳了其若干因素而发展成了迈锡尼希腊语及其他方言?如果这种猜测成立,希腊人的到来就要远早于迈锡尼文明。这是否也能增强“约公元前2100/1900年说”作为正统理论的合法性呢?
结 语
关于希腊人种族起源的研究构成了一个集团长线作战式的较为成功的学术范例。研究者虽尚未搞清该问题的每一细节,但已提供了诸多富有框架意义的答案。对同类及其他若干领域,其经验也具有广延性,它动用的各类技术方案和手段昭示了研究理路的多种可能。
经过不断争论和筛选,在希腊人种族起源研究领域内,起源神话和传说越来越不再被视为有效可用的史料而趋于被淘汰,历史实证主义的方法遭到批评而没落。这提示我们,史料的类别和性质是须首要考虑的因素,对于神话传说历史性的迷信亦应打破,传统文献首先要接受严格的“史料批判”,且不能被当作历史语言学、考古学和基因学研究的导引。这对于我们长时间内以传统文献为导向的“三代”考古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是一条十分有益的经验。
历史语言学能够最先在原始印欧语重构和原始印欧人历史研究方面获得成功,固然跟印欧语系有更多的语言在更早的年代被记录下来有关。但语料问题并非制约研究的唯一因素。近些年来关于上古和原始汉语、汉藏语系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这些成果未能被充分利用到中国早期历史的研究当中。与西方学界在古代史和史前史领域长久以来惯于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多学科联手、协同攻关的学术传统不同,我们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多不关心历史语言学的成果,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合作更多体现在对于传统文献的共同信念的基础上。跨学科研究和多学科合作理应成为未来中国上古史和史前史研究的主流路径。
当下,在全球史的理论探讨持续升温之际,人们更呼唤将该理论加以贯彻的个案研究更多问世。希腊人种族起源研究,不单以希腊为对象,其观察场景还包括地中海、近东、欧亚草原,乃至一大片旧大陆,它关注的主题又是“联系”。它够得上是具有全球史视野、性质和意义的研究个案。而且,在全球史理论热浪翻滚之前,它就以其严谨的专业技术性实践着全球史的理念。正因如此,它不仅能构成全球史的一个案例,而且为全球史提供了一种范例。
本文原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注释从略,谨此致谢!
转自:关天学社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