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中抑郁和焦虑障碍的结局:来自纵向芬兰健康2011研究的结果
摘要
研究目的 :我们调查了一般人群样本中具有终生抑郁和焦虑疾病病史的年轻人的疾病结局及结局预测因子。
材料与方法 :研究样本来自一项针对19至34岁芬兰人的全国代表性两阶段整群抽样。原始研究于2003–2005年进行,随访调查在2011年开展。我们研究了根据SCID访谈被诊断为患有抑郁或焦虑障碍的参与者(排除仅患单一特定恐惧症者)(DAX组,N¼ 181)。对照组包括无DSM‐IV诊断的个体(N¼ 290)。
在2011年通过M‐CIDI访谈对参与者进行了随访,评估其12个月内的抑郁和焦虑障碍。
结果 :2011年,DAX组中有22.8%的参与者被诊断为抑郁或焦虑障碍,而对照组中这一比例为9.8%。DAX组的教育水平低于对照组,生活质量也比对照组差。在DAX组中,2011年获得诊断的参与者比处于缓解状态的参与者生活质量更差,这强调了当前疾病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基线时情绪障碍问卷(MDQ)得分较高可预测2011年生活质量较差。
结论 :因此,抑郁和焦虑障碍在四分之一的参与者中表现为持续性/复发性,显著影响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患有这些疾病的年轻人需要支持以实现他们的学业目标。
1. 引言
抑郁和焦虑障碍通常具有慢性或波动性的病程,且容易复发[1–5]。正式康复后出现残留症状也十分常见[4,6]。因此,由于发病年龄通常较早,某些焦虑障碍甚至在儿童期就已发病,这些疾病可能对患者的生活产生长期影响[7]。
根据最近的人群研究,在一般人群样本中,60–76%的抑郁障碍患者可达到缓解[8–10]。对于焦虑障碍,不同年龄组各种疾病的缓解率报告为53%至78%[11–14]。根据临床研究,重度抑郁症的恢复概率和复发概率均高于焦虑障碍[15,16]。从抑郁症转变为焦虑症的情况较为常见,抑郁障碍与焦虑障碍的共病情况也十分普遍[6],{v23}–21]。
在关于抑郁和焦虑障碍病程预测因素的先前研究中,有关性别和年龄等社会人口学因素的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8,12–14,22–30]。较低教育水平、低收入、失业、处于未婚或无子女与这些疾病的不良结局相关[31,32]。临床特征,如严重程度和症状持续时间,以及共病,也被认为是两种疾病病程不利的风险因素[6,11,16,22,23,28,33–35]。
精神障碍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显著:在芬兰的一项研究中,控制其他疾病和人口社会学变量后,焦虑障碍对个体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的负面影响位居第二,抑郁障碍位居第三[36]。
本研究基于一项全国性的、具有代表性的年轻芬兰成年人(年龄20‐34岁)人群样本及其随访数据。本研究旨在描述抑郁和焦虑障碍在初始评估后六至八年内的持续/复发情况;探讨这些疾病对社会人口学因素和生活质量的影响;并确定可能预测这些疾病病程或影响生活质量的社会人口学相关因素、治疗相关因素以及心理健康评估量表。
2. 方法
2.1 样本
健康2000(http://www.terveys2000.fi/)研究是一项基于全国代表性两阶段整群抽样方法的综合性健康调查,共包括8028名年龄为≥30岁的成人(成人样本)和1894名年龄为18–29岁的个体(青年成人样本)。原始青年成人评估于2001[37]年进行。芬兰青年早期心理健康(MEAF)是一项针对青年成人样本心理健康的随访研究,于2003–2005年间开展。该研究采用两阶段研究设计。首先向整个青年成人样本邮寄了以心理健康为重点的问卷。根据心理健康筛查结果,所有筛查阳性者以及部分随机选取的筛查阴性者被邀请参加心理健康评估,评估内容包括DSM‐IV结构化临床访谈(SCID‐I)和神经心理学评估。MEAF研究的研究流程及心理健康筛查的详细情况此前已有报道[38,39]。
健康2011调查(www.terveys2011.info)是健康2000调查的随访。所有在健康2000调查中的参与者,只要仍存活且居住在芬兰,并且未拒绝参与,均被邀请参加此次随访。数据收集时间为2011年8月至12月。补充数据收集(家庭访谈并进行简化的健康检查或电话访谈)于2012年1月至6月进行。
赫尔辛基和乌西玛医院区伦理委员会批准了健康2000和2011以及MEAF研究。参与者提供了书面知情同意[40]。
2.2 精神科评估
2003–2005年期间,对MEAF参与者采用DSM‐IV结构化临床访谈研究版(SCID‐1)[41]评估精神疾病。最终诊断评估还参考了心理健康治疗接触的病例记录[38,39]。
在2011年随访研究中,由医疗专业人员使用慕尼黑综合国际诊断访谈(M‐CIDI)[42,43]进行诊断评估。该M‐CIDI版本依据DSM‐IV标准评估了八种诊断的12个月患病率:惊恐障碍、广场恐惧症、社交恐惧症、广泛性焦虑障碍、持续性抑郁障碍、重度抑郁症、酒精滥用和酒精依赖。
2.3 参与者
在当前研究中,我们纳入了那些在基线时有抑郁障碍终生诊断(重度抑郁症 [n ¼ 111]、持续性抑郁障碍 [n ¼ 4] 或未特定的抑郁症 [n¼ 30])或焦虑障碍(惊恐障碍 [n ¼ 25]、广场恐惧症 [n ¼ 7]、强迫症 [n ¼ 5]、社交恐惧症 [n ¼ 23]、特定恐惧症 [n ¼ 19]、创伤后应激障碍 [n ¼ 6]、广泛性焦虑障碍 [n ¼ 3]、未特定的焦虑障碍 [n¼ 23]),同时排除了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以及没有其他焦虑或抑郁疾病的特定恐惧症患者。此组此后称为DAX组。样本量为181人。其中,136人(75.1%)参加了2011年随访研究的至少一部分,而92人(50.8%)参加了CIDI访谈。对MEAF参与者在2011年是否参加CIDI访谈的比较结果显示(见补充表1),女性和教育水平较高者更常参与,但在基线时随访参与者与非参与者在精神病症状方面无差异。
为了将DAX组的结果与健康对照组进行比较,我们从MEAF研究中选取了在基线时未获得任何DSM‐IV诊断的参与者。该对照组由290名参与者组成,其中223名(76.9%)参与了健康2011研究的至少一部分,168名(57.9%)参加了CIDI访谈。MEAF参与者中患有抑郁或焦虑障碍以及基线时无DSM‐IV诊断的参与者在2011年随访研究中的研究流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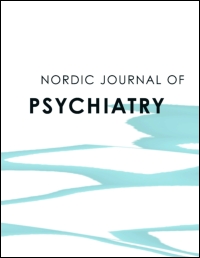
2.4 随访时的参与者特征
2011年参与者特征的信息通过结构化访谈获得。教育水平分为两类:(1)基础(无高中或职业学校)或中级(高中或完成职业学校)和(2)高级(高等职业教育机构、理工学院或大学学位)。婚姻状况分为已婚或同居,以及未婚(单身、分居或丧偶)。当前就业情况分为受雇、学生、失业或其他。
酒精风险使用通过包含三个项目的酒精使用障碍识别测试(AUDIT)问卷进行测量,女性临界点为 ≥5,男性临界点为 ≥6[44]。此外,通过询问参与者当前用药情况,评估抗抑郁药、抗焦虑药、镇静催眠药和抗精神病药物的使用情况。
2.5 结局变量
我们使用2011年CIDI诊断的抑郁或焦虑障碍作为主要结局变量。在基线与随访研究期间,我们没有关于心理健康状况的信息。因此,2011年的发作可能是复发性或慢性疾病,或者该疾病可能已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抑郁或焦虑障碍。使用的第二个结局变量是2011年的主观生活质量,该变量被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回答类别:很差、差和既不好也不坏;第二类包括回答类别:好和很好)。
2.6 可能的基线预测因子
我们研究了基线时不同变量与结局变量之间的关系。使用社会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基础教育、婚姻状况和就业状况。基线时的诊断组和共病情况(仅抑郁症、仅焦虑症、两种疾病均有)也被考虑在内。
治疗对结局变量的影响通过两个变量进行考察:是否接受过(1)任何治疗和(2)最低充分治疗。抑郁症的最低充分治疗定义为在12个月内接受至少两个月的抗抑郁药物治疗,并至少四次就诊于医生,或至少八次心理治疗,或四天住院[39]。对于焦虑障碍,最低充分治疗的标准基本相同,但药物治疗中也接受丁螺环酮作为充分治疗[45]。
我们还研究了不同心理健康量表的得分是否能预测2011年的结局。这些量表包括用于评估一般心理困扰的K10(凯斯勒心理困扰量表)[46]和GHQ(一般健康问卷)[47],用于躁狂症状的MDQ[48],以及用于酒精滥用的CAGE(减少饮酒、感到烦恼、内疚、晨饮)问卷[49]。
此外,焦虑程度通过一个单一问题(“特质焦虑”)进行测量,即询问“您是否通常感到紧张或痛苦”,这在之前的芬兰研究中被用于衡量焦虑程度[50]。
2.7 统计分析
在统计分析中,必须考虑抽样设计以及所有阶段的损耗,尤其是在2011年的随访研究中的损耗。我们使用逆概率加权(IPW)来调整无应答[51]。
我们首先比较了DAX组中在2011年有抑郁或焦虑症12个月患病率的参与者与在2011年处于缓解期的参与者的特征。我们分析了这些组别在社会人口学因素、酒精风险使用、自评生活质量以及精神科药物使用方面的差异。接下来,我们使用相同的变量将DAX组的参与者与基线时无任何DSM‐IV诊断的参与者进行比较。差异检验采用加权的χ²检验或在适当时使用费希尔精确检验。
我们还研究了基线社会人口学因素、诊断组、治疗变量或心理健康评估量表是否能够预测抑郁或焦虑障碍的持续/复发或自评生活质量。采用加权的χ²检验或t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来分析差异。
使用逻辑回归分析来确定与持续性独立相关的变量。性别、基础教育、婚姻状况、治疗变量以及MDQ、K10和CAGE问卷的结果被同时纳入逻辑回归模型,以探讨预测结局的因素。使用权重来校正无应答情况。
在所有统计检验中,p<.05被视为具有统计学显著性。我们使用SAS 9.3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
3. 结果
3.1 2011年DAX组的随访信息
在2011年的随访研究中,DAX组中有92名参与者接受了CIDI访谈,其中包括25名男性和67名女性(表1)。其中,22.8%被诊断为患有抑郁症或焦虑症;18.9%患有抑郁症,10.5%患有焦虑症,6.6%同时患有这两种疾病。基线及随访时抑郁症和焦虑症诊断的更多信息见补充表2。
在CIDI访谈中被诊断为抑郁或焦虑障碍的个体,在社会人口学因素、酒精风险使用或精神科药物使用方面,与处于缓解期的个体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显著性。然而,无当前诊断个体的自报生活质量较好,且该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表1)。
3.2 DAX组参与者与对照组参与者的结局比较
就性别分布而言,两组存在显著差异:在DAX组中,有123名女性(62.8%)以及53名男性(37.2%),而对照组包括147名女性(51.9%)和138名男性(48.1%)。在2011年,对照组的教育水平高于DAX组,但在当前就业状况或婚姻状况方面两组之间无差异。
2011年自报生活质量在对照组中显著优于DAX组参与者。此外,对照组在2011年被诊断为抑郁或焦虑障碍的比例(9.8%)低于DAX组(22.8%)。两组之间的酒精风险使用情况没有差异。DAX组中抗抑郁药物使用更为常见,但两组在抗焦虑药、催眠药或抗精神病药物使用方面无统计学显著差异(表2)。
我们还使用加权的χ²‐检验比较了三个组别之间的生活质量:(1)基线时无诊断的MEAF参与者;(2)DAX组中在2011年未被诊断为抑郁或焦虑障碍的参与者;(3)DAX组中在2011年被诊断为抑郁或焦虑障碍的参与者。2011年,前三组中生活质量好或非常好的比例非常接近(分别为90.3%和89.1%),而第三组则显著较低(39.6%)(p <.0001)。
3.3 2011年抑郁或焦虑疾病持续性相关的基线变量
在双变量分析中,基线调查期间的社会人口学因素与2011年CIDI诊断的抑郁或焦虑障碍无关,接受任何治疗或充分治疗也无关联。仅患有抑郁或焦虑障碍的人群中,其12个月患病率的概率没有差异。
表1。2011年随访信息,关于在2011年参与CIDI访谈的MEAF参与者中具有抑郁或焦虑障碍终生诊断(DAX组)的情况。
| 变量 | 类别 | 全部 (N¼92) | CIDI:焦虑或抑郁的诊断 在2011年 是 (N¼22) | 否 (N¼70) | p |
|---|---|---|---|---|---|
| Sex | Male | 33.6 | 26.8 | 35.6 | .46 |
| Female | 66.4 | 73.2 | 64.4 | ||
| 教育水平 | 基础,中级 | 42.2 | 45.6 | 41.2 | .72 |
| High | 57.8 | 54.4 | 58.8 | ||
| 已婚或同居 | Yes | 82.6 | 81.8 | 82.9 | 1.00d |
| 当前就业状况 | 受雇 | 75.0 | 68.2 | 77.1 | .15 d |
| 学生 | 7.6 | 13.6 | 5.7 | ||
| 失业 | 3.3 | 9.1 | 1.4 | ||
| 其他 | 14.1 | 9.1 | 15.7 | ||
| 自评生活质量 | 好或非常好 | 77.3 | 40.9 | 89.4 | <.0001 d |
| 差或非常差,不好不坏 | 22.7 | 59.1 | 10.6 | ||
| 酒精风险使用e | Yes | 27.2 | 43.1 | 22.3 | .06 |
| 抗抑郁药物使用 | Yes | 13.0 | 9.1 | 14.3 | .72 d |
| 抗焦虑药物使用 | Yes | 2.2 | 4.6 | 1.4 | .42 d |
| 催眠药物使用 | Yes | 3.3 | 9.1 | 1.4 | .14 d |
| 抗精神病药物使用 | Yes | 1.1 | 4.6 | 0.0 | .24 d |
注:a除使用Fisher’s精确检验外,百分比均采用权重计算。bN值未加权。c p值表示通过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在诊断状态分布中各类别间差异的显著性。p<.05以粗体显示。d使用了Fisher’s精确检验。e酒精风险使用通过包含三个项目的酒精使用障碍识别测试(AUDIT)问卷测量,女性和男性的临界点分别为 ≥5和 ≥6。
表2。DAX组和对照组的2011年随访信息。
| 变量 | 类别 | 全部 (N¼471) | 基线时无任何DSM IV‐诊断 (N¼290) | 基线时伴有抑郁或焦虑障碍 (N¼181) | p |
|---|---|---|---|---|---|
| Sex | Male | 43.8 | 48.1 | 37.2 | .04 |
| Female | 56.3 | 51.9 | 62.8 | ||
| CIDI诊断的抑郁或焦虑障碍 | Yes | 14.5 | 9.7 | 22.8 | .005 |
| No | 85.5 | 90.3 | 77.2 | ||
| 教育水平 | 基础,中级 | 37.8 | 33.2 | 44.6 | .03 |
| High | 62.2 | 66.8 | 55.4 | ||
| 已婚或同居(问卷) | Yes | 77.4 | 79.0 | 74.9 | .37 |
| 当前就业状况 | 受雇 | 82.0 | 84.7 | 77.7 | .33 |
| 学生 | 5.2 | 3.7 | 7.6 | ||
| 失业 | 3.0 | 3.2 | 2.6 | ||
| 其他 | 9.8 | 8.3 | 12.1 | ||
| 自评生活质量 | 好或非常好 | 85.3 | 90.3 | 76.6 | .004 |
| 差或非常差,不好不坏 | 14.7 | 9.7 | 23.4 | ||
| 酒精风险使用e | Yes | 28.0 | 29.3 | 25.9 | .57 |
| 抗抑郁药物使用 | Yes | 8.4 | 4.1 | 14.7 | .0005 |
| 抗焦虑药物使用 | Yes | 2.5 | 1.8 | 3.7 | .31d |
| 催眠药物使用 | Yes | 2.0 | 1.4 | 3.0 | .43d |
| 抗精神病药物使用 | Yes | 0.9 | 0.9 | 0.7 | 1.00d |
注:a除使用费希尔精确检验外,百分比均采用权重计算。bN值未加权。c p值表示通过卡方检验或费希尔精确检验测试的诊断状态分布中各类别间差异的显著性。p<.05以粗体显示。d使用了费希尔精确检验。e酒精风险使用通过包含三个项目的酒精使用障碍识别测试(AUDIT)问卷测量,临界点为女性 ≥5,男性 ≥6。
年轻人中抑郁和焦虑障碍的结局:来自纵向芬兰健康2011研究的结果
3. 结果
3.4 与2011年生活质量相关的基线变量
根据双变量分析,基线时的社会人口学因素与DAX组在2011年自报生活质量无关。在随访中,接受任何治疗或充分治疗均不能预测生活质量。诊断组对该结局也无影响(表3)。
基线时MDQ得分较低与随访时更好的生活质量相关。其他问卷不能预测生活质量(表4)。
3.5 抑郁或焦虑障碍及2011年生活质量的持续/复发预测因素;多变量分析
根据多变量分析,基线时选定的预测因子均与2011年M‐CIDI诊断的抑郁或焦虑障碍无关。然而,在调整其他因素后,MDQ得分较低与2011年更好的生活质量相关(比值比 0.82,95% 置信区间 0.69–0.97)(表5)。
4. 讨论
在我们的研究中,基线时有终生抑郁或焦虑障碍诊断的年轻人中,22.8%在2011年被诊断为抑郁或焦虑障碍,而对照组的患病率为9.7%。这一结果比以往基于人群的研究更为有利。
在NEMESIS研究的成人样本中,报告的缓解率较低:基线时有12个月CIDI诊断为抑郁或焦虑症的参与者中,60.7%在七年随访时不再符合这些诊断标准[9]。在精神病理学早期发展阶段研究—另一项关注青少年和年轻人的纵向研究—,抑郁和焦虑障碍的结局与我们的结果相当相似[4,52—54]。在NEMESIS研究中,基线时患有抑郁症的人比患有焦虑症或共病状态的人更可能摆脱诊断[9],而我们未发现不同诊断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与对照组相比,有焦虑或抑郁症病史的参与者教育水平较低,这可能表明这些精神障碍影响了他们的学业成就。以往研究也发现了这种关联,但尚不能确定是精神障碍导致了较低的教育水平,还是较低的教育水平成为精神障碍的风险因素[55–57]。在本研究中,2011年时参与者的当前就业状况或婚姻状况均无显著差异。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不同,研究表明,青少年抑郁和焦虑障碍与不良结局相关,包括工作和家庭关系[57,58]。我们的参与者年龄稍大一些,似乎在青年期之前或期间患有疾病特别影响了他们的教育,而教育通常是在这一年龄段完成的。
有趣的是,治疗(接受过任何治疗或充分治疗)似乎并未影响抑郁或焦虑障碍的预后。这可能是由于在之前多项研究中发现的偏倚所致:症状更严重的个体通常比症状较轻的个体更倾向于寻求并接受治疗,尤其是在专业的心理健康护理中[31,59–61]。而症状严重程度本身已被确定为这些疾病病程不良的风险因素。因此,例如在NEMESIS研究中,使用专业护理似乎是不良结局的最强预测因子,而在重度抑郁症患者中,更密集的治疗与一年随访时较差的结局相关[23,62]。一些其他研究则未发现治疗与结局之间存在关联[16,63]。一个挑战在于研究治疗可能影响的问题在于,这些参与者接受的治疗质量差异很大,而且也存在治疗中断的情况[39,45]。由于样本量相对较小,无法分析治疗的任何组成部分是否与更好的结果相关。
2011年,DAX组参与者自报生活质量比对照组更差。然而,DAX组中较差的生活质量与2011年被诊断为抑郁或焦虑障碍相关,而在2011年已处于缓解状态的DAX组参与者的生活质量则与对照组非常相似。该结果与Markkula等人[6]对健康2000调查成人样本进行的类似随访研究结果略有不同。他们发现,基线时抑郁但随访时未抑郁的受试者,其通过五项EQ‐5D测量的生活质量低于一般人群。我们的结果强调了当前疾病状态对生活质量自我评估的影响。另一个可能解释这种差异的因素是,EQ‐5D会考虑躯体症状以及自我照顾方面的困难,因此可能更善于检测残留症状,这些症状在老年人群中可能表现为躯体症状。然而,我们的发现与国家共病调查复现一致,在该调查中,重度抑郁症的终生病史对目前处于缓解期个体的社会、认知或角色功能没有影响[20]。
在我们的研究中,当前症状(通过K10问卷测量)与疾病持续性相关,这与Markkula等人[6]对抑郁症的研究结果一致。然而,这一结果在多变量分析中并不显著。只有MDQ问卷得分能够预测2011年的生活质量:在MEAF中报告有类躁狂症状的参与者在2011年的生活质量更差。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抑郁障碍中的轻躁狂特征与抑郁发作缓解后较低的生活质量相关[64]。然而,MDQ筛查中的若干问题也可能与个体调节自身情绪和行为的能力有关。在Baryshnikov等人的研究[65]中,用于边缘型人格障碍特征的MDQ和MSI(麦克莱恩筛查工具)似乎在情绪障碍患者中部分测量了相同的维度。因此,对个人生活的控制感可能在生活质量中起着重要作用。有趣的是,Carta及其同事发现,由MDQ阳性导致的更差生活质量(通过简明健康调查表测量)独立于共病情况(情绪、焦虑和进食障碍),支持了MDQ阳性识别出一个独立于精神科诊断之外的特定痛苦领域的假设[66]。
本研究的优势在于对抑郁和焦虑障碍具有较长的随访期,这在一般人群研究中较为罕见,且重点关注了青年期。然而,我们在该期间内仅有一个随访时间点持续六到八年。因此,尚不清楚2011年抑郁和焦虑障碍的发作是否为复发性或持续性疾病。此外,一些疾病可能未被识别,因为2011年随访使用的CIDI版本未包括强迫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特定恐惧症和双相情感障碍。我们未分析基线或随访时的疾病严重程度。
研究设计的主要局限性是失访,这尤其影响了CIDI访谈。另一个局限性是研究样本量相对较小,导致置信区间较宽,特别是在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中。此外,我们无法分别分析不同疾病或疾病组的结局。另外,未对多重检验进行校正。
5. 结论
在基线研究中患有抑郁或焦虑障碍且我们获得随访信息的年轻人中,每四人就有一人在六到八年的随访后仍患有这些疾病。这些疾病可能影响最终的教育水平,但与就业状况或婚姻状况无明显关联。因此,应特别关注患有这些疾病的年轻人,并为其达成学业目标提供支持。基线时MDQ得分较高与随访时生活质量较差相关,但未发现其他显著的结果预测因素。
表3. 抑郁或焦虑障碍(CIDI诊断)和 2011a生活质量的可能预测因素(基线)
| 基线特征 | 类别 | CIDI:焦虑或抑郁的诊断在2011 是 %b | No %b | p d | 2011年自评生活质量 非常差,bad, not good也不bad %b | 良好,非常好 %b | p d |
|---|---|---|---|---|---|---|---|
| Sex | Male | 26.8 | 35.6 | .46 | 31.6 | 33.83 | .85 |
| Female | 73.2 | 64.4 | 68.4 | 66.2 | |||
| 基础教育 | 高中以下学历 | 59.4 | 46.2 | .29 | 50.5 | 48.8 | .89 |
| 高中 | 40.6 | 53.8 | 49.5 | 51.2 | |||
| 已婚或同居 | Yes | 69.9 | 61.3 | .48 | 72.0 | 59.8 | .33 |
| 当前就业状况 | 受雇 | 54.6 | 60.9 | .51e | 55.0 | 60.0 | .41e |
| 学生 | 18.2 | 18.8 | 20.0 | 21.4 | |||
| 失业 | 13.6 | 4.4 | 15.0 | 4.3 | |||
| 其他 | 13.6 | 15.9 | 10.0 | 14.3 | |||
| 诊断 | 仅抑郁障碍 | 68.2 | 62.9 | .68e | 66.7 | 67.6 | 1.00e |
| 仅焦虑障碍 | 13.6 | 22.9 | 19.1 | 19.7 | |||
| 同时患有抑郁和焦虑障碍 | 18.2 | 14.3 | 14.3 | 12.7 | |||
| 任何治疗 | Yes | 68.0 | 72.4 | .70 | 65.4 | 74.4 | .42 |
| 充分治疗 | Yes | 35.5 | 44.4 | .47 | 43.7 | 43.1 | .96 |
注:a双变量分析。b百分比通过权重计算,使用费希尔精确检验时除外。cN值未加权重。d p值表示通过卡方检验或费希尔精确检验对诊断状态和生活质量分布中类别间差异显著性的检验结果。p<.05以粗体显示。e使用了费希尔精确检验。
表4. 2011年抑郁或焦虑障碍的CIDI诊断和生活质量的可能预测因素(基线)
| 变量 | CIDI:2011年焦虑或抑郁的诊断 是 (N¼22) | 否 (N¼69) | p a | 2011年的生活质量 非常差,差,没有好与不好 (N¼20) | 好,非常好 (N¼70) | p a |
|---|---|---|---|---|---|---|
| 特质焦虑 | 2.2 | 2.2 | .94 | 2.4 | 2.2 | .31 |
| GHQ‐12 评分 | 2.4 | 2.8 | .67 | 2.7 | 2.7 | .96 |
| MDQ 评分 | 3.7 | 3.8 | .94 | 5.3 | 3.1 | .02 |
| CAGE评分 | 1.4 | 1.7 | .51 | 1.4 | 1.7 | .50 |
| K10评分 | 19.1 | 16.3 | .04 | 18.8 | 16.3 | .08 |
注:a p值表示通过t检验对均值在类别间差异的显著性。p<.05以粗体显示。GHQ:一般健康问卷;CAGE:“减少饮酒、感到烦恼、内疚、晨饮”问卷;MDQ:情绪障碍问卷。
表5 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1a. 2011年与CIDI抑郁症或焦虑症及生活质量相关的基线变量
| 基线变量 | 类别 | CIDI:2011年抑郁或焦虑‐障碍 OR | 95% 置信区间 | 2011年生活质量好或非常良好 OR | 95% 置信区间 |
|---|---|---|---|---|---|
| 性别 | 男性(参考) | 1 | 1 | ||
| 女性 | 1.25 | 0.28–5.63 | 0.70 | 0.17–2.88 | |
| 基础教育 | 低于高中学历(参考) | 1 | 1 | ||
| 高中 | 0.56 | 0.17–1.82 | 0.80 | 0.27–2.38 | |
| 已婚或同居 | 否(参考) | 1 | 1 | ||
| Yes | 1.77 | 0.51–6.14 | 0.32 | 0.08–1.25 | |
| 任何治疗 | 否(参考) | 1 | 1 | ||
| Yes | 1.04 | 0.22–4.85 | 2.10 | 0.51–8.64 | |
| 充分治疗 | 否(参考) | 1 | 1 | ||
| Yes | 0.70 | 0.18–2.66 | 0.62 | 0.15–2.64 | |
| MDQ 评分 | 0.94 | 0.77–1.14 | *0.82 | 0.69–0.97 | |
| K10评分 | 1.11 | 0.98–1.26 | 0.96 | 0.85–1.08 | |
| CAGE评分 | 1.01 | 0.66–1.56 | 1.24 | 0.69–2.24 |
注:*p<.05。这些 p值 表示通过卡方检验对各类别间比值比差异的显著性。具有显著性差异(p<.05)的结果以粗体显示。a所有变量均同时纳入一个逻辑回归模型中,并对表中所示的其他因素进行调整。OR¼调整后比值比;95 % CI = 95% 置信区间。GHQ:一般健康问卷;CAGE:“减少饮酒、感到烦恼、内疚、晨饮”问卷;MDQ:心境障碍问卷。




















 74
74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