脂质生物标志物在重度抑郁症中的作用
1. 引言
重度抑郁症(MDD)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目前预计将成为导致残疾的第二大原因 2020[1,2]。
在英国,单次终生发作的重度抑郁症患病率为6.4%[3]。根据《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定义MDD诊断标准的主要症状包括情绪低落、快感缺失和乏力,持续至少两周[4]。
这些症状的存在严重损害了患者的日常功能,并导致生产力下降[5,6]。MDD的预后具有变异性,且常呈慢性病程;据报道,一次发作的中位持续时间为23周,25%的个体在其一生中会经历进一步的发作[7]。除了生活质量降低外,重度抑郁症患者通常比健康个体的预期寿命更短,部分原因是终生自杀率增加[8],,但也由于共病疾病导致的死亡率较高,尤其是心血管疾病(CVD)[9]。此外,持续而广泛的情绪低落使患者的生活质量显著受损。
在临床实践中,重度抑郁症的诊断、管理和治疗面临的诸多挑战源于目前对分子和细胞病理生理学缺乏深入了解。因此,当前的诊疗主要依赖于各种精神科评定量表。尽管这些量表旨在减少主观性和临床医生间差异,但它们在提供全面评估和适当治疗方案方面显然存在不足[10]。除了诊断方面的不足之外,多达30%的患者对抗抑郁药物无反应,被诊断为难治性抑郁症[11]。即使有反应的患者,症状也往往仅得到部分缓解。
并且有人提出,抗抑郁药明显的疗效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安慰剂效应所致[12]。
改善重度抑郁症临床管理的一个潜在途径是使用外周生物标志物而非主观症状评分。如果有效,检测外周生物标志物可能成为诊断和监测重度抑郁症的一种客观、经济、高效且无创的方法。迄今为止的研究已基于多种假说提出了候选生物标志物,其中最显著的是单胺类神经传递、免疫‐炎症、神经可塑性和神经内分泌功能的作用[13]。这些理论大多以蛋白质功能障碍为核心。然而,脂质通过调节转运、锚定和结构支持,在决定蛋白质的细胞功能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此外,脂质对神经元功能至关重要,具有多种功能,包括调控膜流动性和通透性、囊泡形成与运输、神经递质释放、细胞完整性以及可塑性[14,15]。
脂质是一类潜在的外周生物标志物,可用于定量诊断、监测治疗反应和患者分层。其相关性还可能表明存在可通过药物干预或通过膳食补充进行预防的疾病机制。
2. 胆固醇
胆固醇就是这样一种可在外周检测到的脂质,其代谢、运输或数量缺陷可能在重度抑郁症中起作用[16]。全身胆固醇中有20%存在于大脑中,其中70%位于形成髓鞘的少突胶质细胞内[17,18]。尽管胆固醇含量丰富,但其水平受到严格调控,因为它对适当的神经系统发育和功能至关重要[19]。胆固醇存在于质膜中,其位置和浓度会影响膜流动性[20],进而影响膜结合蛋白和离子通道的调节,以及随后的突触传递。此外,它还参与突触形成、树突形成和轴突导向。上述任一过程的失败都会导致神经传导失败和突触可塑性降低。抑郁症患者中发现这些功能中的许多异常发生了改变[21]。
作为人类饮食的一部分,摄入的胆固醇通常吸收不良。相反,胆固醇主要通过复杂的合成途径在人体细胞中合成[22]。这是一个由一系列酶调控的多步骤过程。由于胆固醇无法穿过血脑屏障,大脑中的胆固醇主要通过星形胶质细胞和少突胶质细胞进行循环利用或局部合成。该过程与胆固醇的转运紧密相关。胆固醇通过与载脂蛋白结合形成脂蛋白,在循环系统中进行转运。不同类型的载脂蛋白可形成不同密度的脂蛋白,它们共同调节胆固醇的转运、溶解度和稳定性[23]。尽管外周与中枢神经系统(CNS)代谢之间的关联尚不明确,但已有研究表明,高胆固醇饮食和长期胆固醇补充可改变大鼠的中枢神经系统脂质谱[23],而降胆固醇他汀类药物则可减少豚鼠的脑内胆固醇合成[24]。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明确外周与中枢神经系统胆固醇谱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效应。
2.1. 心血管疾病和重度抑郁症
心血管疾病涵盖了一系列涉及血管和心脏的疾病,常在同时患有重度抑郁症的患者中发现。事实上,与非抑郁症个体相比,抑郁症患者发生冠心病的风险增加2至4倍[25,26]。进一步研究发现,患有重度抑郁症会增加心脏性死亡的风险,有时这种风险独立于基线时的心血管疾病状态[26,27]。相反,在心肌梗死后,急性或慢性抑郁期较为常见,并对患者预后产生不良效应[28–30]。尽管明显存在心血管疾病与重度抑郁症之间的关系,但两者之间是因果关系还是相关关系,仍有待阐明。另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重度抑郁症和心血管疾病是否分别为同一潜在病理生理学过程的早期和晚期并发症。
2.2. 重度抑郁症中的高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
除了心血管疾病外,胆固醇及含胆固醇分子的水平也与重度抑郁症相关。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患有重度抑郁症的抑郁症患者通常表现出总血清胆固醇降低[33–35]。此外,大量研究表明,重度抑郁症患者常出现高密度脂蛋白减少、低密度脂蛋白增加以及LDL/HDL比值升高[21,34,36]。有趣的是,抑郁症状未得到缓解也与总血清胆固醇和LDL胆固醇水平偏低相关[37,38]。除了观察到的HDL和LDL水平差异外,其组成成分载脂蛋白的水平也与重度抑郁症相关[39]。一项病例对照研究显示,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抑郁症患者的低密度脂蛋白及其载脂蛋白B(apoB,低密度脂蛋白的组成成分)循环水平较高,而高密度脂蛋白和载脂蛋白A(apoA,高密度脂蛋白的组成成分)水平较低。
有一些研究不支持这些发现,声称在老年人群队列中低血清胆固醇与抑郁症之间缺乏显著关联 [40,41]。尽管在不同年龄组中检测脂质水平具有重要价值,但在未能充分了解重度抑郁症潜在机制的情况下,很难断定65岁以上的患者是否与年轻患者具有相同的病理过程。一些研究结果存在矛盾,有的报告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血清水平增加,但总胆固醇或高密度脂蛋白水平无变化[42],,而其他研究则报告抑郁症群体的总胆固醇升高[21]。
尽管许多研究表明胆固醇种类与重度抑郁症之间以及后者与心血管疾病之间可能存在关联,但这些关联仍存在不一致之处。一项旨在评估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与抑郁症关系的荟萃分析得出结论:总胆固醇与抑郁症呈负相关,而高密度脂蛋白水平升高则与抑郁症增加相关,尤其是在女性中[43]。此外,最强的关联出现在未经药物治疗的样本中,这提示应对患者进行监测。最近另一项荟萃分析指出,循环中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与抑郁症呈负相关[44]。为了明确胆固醇与抑郁症之间的关系性质,并解决研究结果中的差异,以便使胆固醇在诊断中具有实用价值,还需在不同人群队列中开展更广泛的研究。此外,低密度脂蛋白水平与抑郁症状之间的潜在关系可能受到体重指数(BMI)等因素的混杂影响[45]。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升高与体重指数增加相关,而体重指数本身又与抑郁症状相关。许多研究发现,体重指数增加与情绪障碍(如重度抑郁症)风险增加相关[46,47]。另有研究发现体重指数与重度抑郁症呈负相关,但与其他肥胖指标无显著关联,表明肌肉质量增加而非肥胖可能降低抑郁症风险[48]。
2.3. 胆固醇与其他精神障碍
自杀或自杀意念是重度抑郁症的一种罕见但极具破坏性的症状。重度抑郁症患者的异常胆固醇与自杀倾向增加有关[49]。大量最新数据显示,低循环总胆固醇与自杀倾向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16,50–57]。具体而言,在各种住院和门诊分析中,血清胆固醇水平降低与自杀意念、自杀企图史、更严重且更具暴力性的自杀方式,以及拥有一级亲属死于自杀的可能性增加相关[58–63]。相反,在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中,未发现自杀企图与任何血液脂质值之间存在关联[64]。这表明低胆固醇水平可能与特别严重的重度抑郁症病例相关,或提示存在自杀企图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胆固醇生物标志物有助于识别需要额外监测和支持的特定抑郁症患者群体。
尽管理解重度抑郁症(MDD)的潜在机制将是一个关键进展,但胆固醇与其他精神障碍之间的关系可能为这一主题提供新的见解。广泛性焦虑症(GAD)与血清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LDL)升高以及高密度脂蛋白(HDL)降低相关[65–67]。这并不是说这两种疾病处于同一谱系的对立两端,但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确实表现出一些相反的特征。有趣的是,共病性重度抑郁症和广泛性焦虑症患者呈现出比单一疾病更恶化的血脂谱[65–67]。
其他研究发现,患有其他焦虑障碍(如惊恐障碍、强迫症和恐惧症)的患者血清胆固醇水平升高 [66,68,69],,且低密度脂蛋白和极低密度脂蛋白水平的增加与症状严重程度相关[70]。此外,这些焦虑障碍与重度抑郁症的共病会产生进一步不同的血脂谱[69,71]。可以推断,维持适当的胆固醇水平对于预防抑郁和焦虑障碍均具有重要意义,且其应处于某一最佳范围内。此外,这也表明在考虑将胆固醇作为重度抑郁症的生物标志物时,需要考虑共病疾病的存在。
2.4. 胆固醇的作用机制
血清胆固醇水平与自杀倾向之间负相关关系的分子机制假说认为,这种效应通过影响5‐羟色胺(5‐HT)系统实现,而该系统目前是抗抑郁治疗的主要靶点之一[72]。细胞膜中胆固醇含量较低与体外小鼠分析中测得的5‐HT受体密度降低相关[72–74]。Sun等使大鼠暴露于慢性轻度应激(CMS)28天,结果显示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中的总胆固醇水平显著降低[74]。长期饮食补充可逆转由CMS引起的行为变化。此外,向mPFC注射5‐HT1A拮抗剂可阻断胆固醇补充的治疗效应[74]。这表明,特别是在前额叶皮层中,胆固醇会影响5‐HT1A受体在抑郁症病理学及治疗中的敏感性。然而,抑郁症的5‐羟色胺解释尚不足以完全阐明抑郁症的发生机制,这一点从大量针对5‐羟色胺系统的抗抑郁治疗无效的患者中可见一斑[11,75,76]。
另一种可能的机制是通过改变炎症谱。如前所述,高LDL和低HDL在动脉粥样硬化发生过程中对免疫系统的上调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高浓度的胆固醇会增加高胆固醇血症兔以及体外经胆固醇处理的巨噬细胞中白细胞介素6(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释放[77,78]。IL‐6和TNFα水平在抑郁症患者中通常升高,并在成功的抗抑郁治疗后下降[79,80]。此外,在兔子和人主动脉平滑肌细胞中,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处理导致白细胞介素1β(IL‐1β)的产生增加[81],,这是一种在抑郁症患者中也被发现上调的细胞因子[82]。
2.5. 以胆固醇通路为靶点的抗抑郁治疗
尽管有一些证据表明胆固醇在抑郁症的病理生理学中发挥作用,但它能否成为治疗干预的新靶点仍有待观察。研究表明,患有情绪障碍且血清胆固醇水平病理性降低的个体,在接受心理和/或药物干预后,症状严重程度同时减轻,血清胆固醇水平增加[83]。这表明外周胆固醇的变化与症状减轻同时出现,提示胆固醇生物标志物在监测治疗中的潜在用途。
在重度抑郁症治疗中将胆固醇作为膳食补充剂使用不太可能获得认可。诚然,强化胆固醇治疗在心血管疾病方面产生了积极效果[84]。然而,仅通过饮食方式进行此类治疗的可行性值得怀疑。此外,由于抑郁症与胆固醇水平之间缺乏明确的关系,因此很难推荐任何针对胆固醇水平的治疗。
可能可以通过其他方式靶向胆固醇通路,例如使用降胆固醇他汀类药物。一项使用洛伐他汀作为氟西汀辅助治疗的双盲试验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上的抑郁症改善更为显著[85]。另一项双盲试验表明,阿托伐他汀作为西酞普兰的辅助治疗比单用西酞普兰产生更明显的抗抑郁效果,支持了他汀类药物有助于减轻抑郁症状的观点[86]。此外,总体而言,使用他汀类药物与抑郁症发病风险降低32%相关[87]。已知他汀类药物可减少胆固醇合成并增加外周LDL的摄取,这支持了LDL升高在维持重度抑郁症病程中的作用。此外,还需明确高密度脂蛋白补充是否具有任何益处,因为该领域的研究尚少。
难治性抑郁症的当前治疗方法包括电休克治疗(ECT)和运动[88]。研究表明,ECT会增加总胆固醇水平[89],,而运动则会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并增加高密度脂蛋白水平,这支持了胆固醇可能参与重度抑郁症且可被纠正的观点。
3. 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s)
与胆固醇类似,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s)可在外周循环中检测到,并与重度抑郁症(MDD)相关。构成细胞膜的磷脂由磷酸“头部”、甘油和脂肪酸“尾部”组成。这些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s)来源于亚麻酸(omega‐6)或α‐亚麻酸(omega‐3;图1)。最常见的omega‐6是花生四烯酸,而最常见的omega‐3是二十二碳六烯酸(DHA),其次为其前体二十碳五烯酸(EPA)[90]。仅DHA就占人类脑脂质的15%–20%,该类物质的减少与抑郁症密切相关,原因在于炎症反应失调、抗氧化能力下降以及神经传递紊乱[91]。DHA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中最丰富的omega‐3脂肪酸,尤其在早期发育阶段含量较高[92]。它不存在于植物性食物中,最丰富的膳食来源是富含脂肪的鱼类[93]。
omega‐6多不饱和脂肪酸通常具有促炎性,其主要有害效应被认为是通过竞争性抑制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所致,这表明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具有保护作用[90]。omega‐3和omega‐6多不饱和脂肪酸均为必需化合物,意味着它们只能从饮食中获取(omega‐6主要来源于植物油,而omega‐3主要来自鱼油)。再加上已有证据表明培养的脑细胞的分化和功能需要α‐亚麻酸以及omega‐3和omega‐6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使得脑功能与饮食之间的联系更加清晰[94]。
3.1. 多不饱和脂肪酸绝对水平与重度抑郁症
与非抑郁症对照者相比,已观察到抑郁症患者体内的游离循环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以及红细胞膜中的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均存在不足[95–98]。
此外,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与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更显著降低相关[99]。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较低与抑郁症相关这一观点得到了以下观察结果的支持:在鱼类摄入量较高的国家(鱼类是饮食中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主要来源),抑郁症的发病率较低[100,101]。此外,大量研究发现,在不同人群中,鱼类摄入量与抑郁症发病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102–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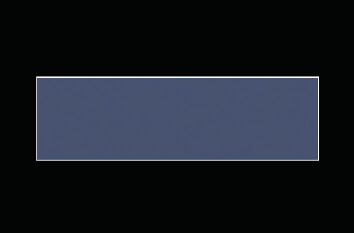
脂质生物标志物在重度抑郁症中的作用
3.2. 多不饱和脂肪酸亚型比例与重度抑郁症
人类最初被认为是在饮食中欧米伽‐6与欧米伽‐3比例为1:1的条件下进化的。在过去100年中,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下降,同时伴随着omega‐6摄入增加,导致膳食脂肪酸比例达到15/16:1[108–110]。这与近年来抑郁症诊断的增加相吻合,表明这种饮食失衡可能在其中起到一定作用[111]。这提示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在重度抑郁症的发展中可能与绝对水平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这一假设得到了多项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观察到抑郁症患者中较高的omega‐6: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比例[95,112–114]。事实上,已有研究发现,在血浆和红细胞中,更严重的抑郁症病例与升高的omega‐6: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比例相关[110,112]。同样,一项纵向研究也显示,基线时升高的omega‐6:omega‐3比例与随时间推移抑郁症状恶化相关,表明可能存在因果关系[115]。尽管有一些研究未能重复这些发现[116,117],,但大多数研究支持较高的omega‐6: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比例与抑郁症相关的观点[118]。显然,重要的不仅是每种多不饱和脂肪酸种类的绝对浓度,更是它们的相对比例。
3.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作用机制
在抑郁症患者中,omega‐3/omega‐6多不饱和脂肪酸作用位点的多种影响正逐渐被观察到。确实,重度抑郁症中已提出存在膜流动性改变,并通过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补充后膜流动性增加得以证实[119,120]。此外,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还影响神经元发育、炎症和神经传递:一种减少在5‐羟色胺能神经传递中的改变与仔猪膳食DHA的减少相平行,并在抑郁症患者中被观察到[121–125]。这与紊乱的胆固醇水平下5‐HT受体敏感性的改变有关[63,126]。尽管其潜在机制尚未阐明,但在重度抑郁症患者中确实存在5‐羟色胺能神经传递的减弱,这一点进一步得到了以下事实的支持:最有效的抗抑郁药物(如氟西汀)属于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s)。研究已证实,某些神经递质(尤其是内源性大麻素)是由脂质合成的[127]。因此,仍有研究空间来确定脂质功能障碍是否对神经递质的合成、储存或释放具有直接效应。
omega‐6多不饱和脂肪酸通常被认为具有促炎作用,而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则被认为具有抗炎的效应。这种炎症平衡基于类二十烷酸的生成,类二十烷酸是作为中枢神经系统和外周炎症调控信使的小分子信号分子。在炎症级联反应过程中,omega‐6前列腺素和白三烯类二十烷酸由花生四烯酸合成。而来源于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类二十烷酸则炎症性较低,甚至具有抗炎的特性[127]。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取代、竞争性抑制或拮抗作用来抵消花生四烯酸衍生的类二十烷酸的影响[128]。这些必需营养素意味着体内omega‐3/omega‐6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和比例由个体的膳食摄入决定,从而决定了类二十烷酸调控的功能。鉴于类二十烷酸在炎症中的作用、其来源于多不饱和脂肪酸以及炎症与重度抑郁症之间的关联,重度抑郁症患者中观察到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降低和omega‐6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升高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DHA缺乏大鼠表现出IL‐6和TNFα[13,129,130]的显著增加,而在DHA水平恢复正常后该现象可逆转[13]。如前所述,IL‐6和TNFα水平在抑郁症患者中通常升高[79,80]。
3.4. 补充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作为一种潜在的抗抑郁治疗
DHA和EPA的给药已成为众多旨在通过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补充来减轻重度抑郁症症状的人类干预研究的重点,结果虽有希望但存在不一致。李等人[131]展示了支持将其用作有效治疗的实质性证据。在接受酯化EPA且原有药物治疗方案不变的患者中,抑郁症状显著减轻。皮特和霍罗宾对二十碳五烯酸在持续性重度抑郁症患者中的效应开展了一项双盲剂量范围研究。该研究表明,低每日剂量EPA可改善抑郁症状,而较高剂量则无治疗效果[132]。
荟萃分析显示,重度抑郁症患者体内的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低于对照组,且补充omega‐3对改善抑郁症状具有显著益处[133,134]。一项纳入15项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共916名参与者的荟萃分析得出结论: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在重度抑郁症及相关情绪障碍中是一种有效且安全的抗抑郁治疗手段[135]。该荟萃分析包括了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作为现有抗抑郁治疗增效方案的研究。此外,该分析还指出,EPA作为抗抑郁剂比DHA更有效,且当配方中EPA比例高于DHA时,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治疗效果最佳。最近一项关于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治疗重度抑郁症的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表明,在方法学质量较差、持续时间较短以及基线时抑郁症状更严重的患者中,该干预措施仅呈现出非显著性的疗效趋势,而13项试验未显示显著益处[136]。这些数据表明,总体而言,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补充可能代表一种潜在的抗抑郁治疗策略,至少在某些人群队列中如此。鉴于现代西方饮食通常缺乏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种治疗可能仅仅纠正了这一失衡状态。
目前尚无研究探讨减少欧米伽‐6多不饱和脂肪酸摄入是否具有任何益处。
人类研究也表明,二十二碳六烯酸膳食补充可能有助于减少攻击性等与压力相关的行为[137–139]。尽管这些研究在规模上有限,且未包含精神健康患者,但综合来看,它们进一步支持了通过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补充来改变行为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集中在鱼类摄入量自然非常高的群体[100,102],而针对重度抑郁症患者进行的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补充试验则得出了不明确的结果。
到目前为止,人类研究已取得有希望的结果。然而,仍需开展更多基于更大人群队列的可重复试验,以评估这些发现的重要性。不过,已有大量动物研究表明,在某些情况下,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可能是治疗重度抑郁症的潜在疗法。饮食中缺乏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大鼠和小鼠会表现出抑郁样行为以及学习能力缺陷,而通过在饮食中补充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可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这些症状[140–142]。这表明,当存在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缺乏时,其补充可能产生部分抗抑郁效应。此外,这些研究发现,虽然缺乏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饮食会降低大脑中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但补充后可逆转这一改变[140–142]。这些论文提出了一个问题:脑脂质状态的重要性是在哺乳和发育期间确立的,还是在成年期仍存在发生改变的可能?
3.5. 酶在脂肪酸代谢中的作用
关于多不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目前尚不清楚功能障碍发生在代谢通路的哪个环节。有研究提出,可能涉及负责神经元脂肪酸代谢的酶(如长链酰基辅酶A合成酶(LACS‐2))以及参与内源性大麻素调节的酶(如脂肪酸酰胺水解酶(FAAH))发生了改变。长链酰基辅酶A合成酶是大脑中脂肪酸代谢的关键酶[143]。在暴露于习得性无助范式的抑郁症动物模型大鼠中,观察到LACS‐2 mRNA表达增加。这一趋势在84%被检测的大脑区域中均存在,包括前额叶皮层[144]。此外,在表现出类似抑郁症症状的大鼠中,其前额叶皮层和海马体中的FAAH水平也更高[145]。未来需要进一步分析脂肪酸代谢在重度抑郁症中与其他信号系统(除内源性大麻素系统外)相关的神经回路功能作用,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仍有限。将针对酶活性的分析与对重度抑郁症中血脂谱紊乱的进一步分析相结合,有望在未来发现可用于治疗干预的特异性靶点。
4. 其他脂质生物标志物与重度抑郁症
尽管本综述主要关注胆固醇和多不饱和脂肪酸作为抑郁症生物标志物的潜在作用,但还有许多其他脂质种类与重度抑郁症相关,包括甘油酯、鞘脂、甘油磷脂和甘油三酯[23]。这并不是说它们的重要性较低,而是支持其在抑郁症中作用的证据较少。此外,虽然单个脂质种类的血清浓度已与重度抑郁症相关联,但考虑由多种目标脂质种类组成的整体血脂谱可能更有意义,甚至可结合更传统的肽类和代谢物生物标志物一起分析[146]。
除了脂质分子外,还有许多与脂质种类的摄入、转运和代谢相关的基于肽的生物标志物。瘦素和神经肽Y这两种肽均参与食欲控制和能量稳态[147,148],并与应激和抑郁症相关[149–151]。这些参与脂质稳态的肽类生物标志物可用于补充对抑郁症中脂质生物标志物的监测。
5. 讨论
最近的研究强调了监测外周PUFAs和胆固醇在MDD的预测、分层和管理中的潜在作用(图2)。然而,关于HDL和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相互减少以及LDL和omega‐6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增加等初步结论,仍需进一步分析,以充分理解其与抑郁症生物标志物之间的关系。首先,有必要明确脂质稳态的这些变化究竟是重度抑郁症病理生理学的驱动因素,还是该疾病的一个后果。当然,如果这种效应是因果的,那么这些脂质摄入或代谢的改变驱动抑郁症的病理生理学的可能性,远大于抑郁症导致脂质减少的可能性。此外,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变化是由摄入或代谢改变引起的。这为确定酶在脂质合成中与精神疾病相关的作用提供了研究空间。此外,可能仅在部分患者中观察到这种关系。这使得有可能根据患者的脂质生物标志物谱来定义抑郁症亚型。
已知炎症过程至关重要,对多不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的进一步研究可能会揭示这些因素在重度抑郁症病理学中的复杂关系。事实上,已有研究表明,增加的高密度脂蛋白和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可能对抑郁症介导的炎症具有保护作用[74,152]。炎症过程的具体机制仍把蛋白质功能障碍视为重度抑郁症病理生理学的关键方面,但脂质的作用正被证明同样重要,尤其是因为分子水平上的蛋白质功能在很大程度上由脂质功能决定。

尽管现代抗抑郁药物可能有效,但处方方案仅能使38%的患者在临床上得到部分改善[62]。毫无疑问,有必要确定新的治疗靶点,并制定更有效的MDD治疗方法。目前MDD的药物治疗间接影响的两条常见通路是神经保护和抗炎[153]。这两个过程也是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作用靶点,使得多不饱和脂肪酸在MDD中的潜在作用颇具前景。鱼类摄入量较高的人群表现出较低的MDD患病率,且重度抑郁症患者的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较低[102],,这表明该分子家族可能具有保护作用,尽管产生这种效应的精确分子机制仍有待确定。当然,并非所有涉及补充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研究都显示出症状的显著改善,但重度抑郁症病理生理学的异质性可能需要多种同时补充。某些患者对特定药物反应更好,表明在影响诊断、预后和治疗反应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方面,重度抑郁症具有复杂性[154]。此外,未来或许可以在重度抑郁症中进行亚分类,从而更明确地定义并对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敏感的抑郁症进行针对性治疗,以期获得更有效的结果。如果确实如此,omega‐3补充的一大优势在于其无已知副作用、安全且具有成本效益。从这个角度来看,识别可能对这种辅助治疗产生反应的患者将完全有益。话虽如此,由于所需剂量未知且可能较大,通过补充omega‐3来增强现有疗法可能并不可行。
6. 结论
问题仍然在于,是否有足够的证据将脂质应用于重度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当然,未来进行进一步分析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考虑到补充剂的提供以及外周血标志物的测量都具有简便性和低成本。
对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补充的反应差异表明,在未来更大规模的队列研究中,可根据症状和抑郁症严重程度对患者进行分层,从而促进更具体和针对性的方法用于诊断和治疗。这为更大规模的试验留下了空间,以评估这些以及其他脂质生物标志物是否如迄今为止的研究所示那样重要。























 2743
2743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