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医学中的诊疗一体化方法:现状与未来前景
摘要
引言:诊疗一体化是一个新兴领域,通过将诊断与特定靶向治疗相结合,实现对患者的个体化治疗。在核医学的临床实践中,诊疗一体化通常利用相同的分子标记两种不同的放射性核素,一种用于成像,另一种用于治疗。
涵盖领域:作者回顾了不同放射性药物在相关领域的临床应用,包括放射性碘在分化型甲状腺癌中的成熟应用、放射性标记的间碘苯甲胍(MIBG)在神经母细胞瘤中的应用以及肽类放射性核素受体治疗(PRRT)在神经内分泌肿瘤管理中的临床影响。此外,还将回顾更为前沿且近期引入的诊疗一体化方法,例如使用177Lu‐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SMA)的放射性配体疗法以及在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中的靶向α治疗。最后,将介绍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在适合非放射性核素靶向治疗的生物标志物成像方面的主要应用。
专家观点:诊疗一体化正迎来一种革命性的临床方法,这种方法与个体化医疗的概念密切相关,并以“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为核心。从这一角度来看,诊疗应用将需要经过良好培训的专家,他们不仅能够管理该学科的技术方面,还能够在多学科环境中应对更具创新性的肿瘤治疗。
关键词:诊疗一体化;核医学;神经母细胞瘤;MIBG;神经内分泌肿瘤;DOTA‐肽类; PSMA;微球
文章亮点
- 诊疗一体化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学科,它将诊断与靶向治疗相结合,以实现个体化临床方法。
- 诊断阶段旨在识别能够预测治疗反应的特异性生物标志物,并可用于治疗期间对患者的监测。
- 在核医学中,诊疗一体化方法通常通过使用相同分子(或尽可能相似的两个分子)来实现,这些分子要么标记不同的放射性核素,要么使用相同放射性核素但在不同剂量下应用。
- 在诊断阶段,通常使用γ射线发射型放射性核素(如 123I),尽管应优先选择正电子发射体(如 124I),因为PET技术可获得更高质量的成像和定量结果。
- 使用 131I对分化型甲状腺癌进行放射性碘(RAI)治疗是诊疗一体化方法的首个范例。自其引入核医学以来,人们已做出诸多努力以实现准确且个体化的剂量测定。
- 使用 123I(用于诊断目的)或 131I(用于治疗)标记的间碘苄胍(MIBG)已应用于晚期化疗耐药的高危神经母细胞瘤的治疗,并取得了有希望的结果。
- 经过20多年的临床试验,诊疗一体化放射性药物 177Lu‐DOTATATE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的批准,商品名为Lutathera®,用于治疗进展性神经内分泌肿瘤。
- 在使用诊疗一体化放射性药物68Ga‐PSMA‐11/177Lu‐PSMA‐617治疗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方面已获得有希望的结果。
- 使用新型PET探针(即 89Zr‐trastuzumbab)进行分子影像是一种用于患者筛选和监测非放射性核素靶向治疗反应的有前景的工具。
1. 引言
在古罗马神话中,Janus Bifrons是过渡与二元之神,通常被描绘为拥有两张朝向相反方向的面孔,象征着从过去到未来的过渡,也代表着从一种视角转换到另一种视角的能力。根据这一隐喻意义,所谓的“诊疗一体化”学科可被视为现代医学的双面神雅努斯,因为它成功地将治疗与诊断相结合,旨在创建一种独特方法[1]。“诊疗一体化”一词(也称为“theragnostics”)由PharmaNetics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芬克豪泽于1998年首次提出[2]。
尽管诊疗一体化涉及越来越多的科学学科,尤其是在纳米技术领域[3], ,但这种创新医疗方法与核医学密切相关。事实上,放射性核素成像提供了独特的机会,可通过使用某种标记有适合成像辐射发射同位素的放射性药物来检测和量化特定肿瘤生物标志物的表达;随后,同一种放射性药物可标记发射α或β粒子的放射性核素,以实现杀瘤效应[4]。在这一背景下,放射性碘(131I)可能是诊疗一体化最早的应用,因为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术后对残留组织的消融正是基于甲状腺滤泡细胞能够摄取 131I的特性,而 131I既发射伽马射线(即用于诊断),也发射β粒子(即用于治疗)[5]。因此,同一种元素既可用于检测亲碘性残留甲状腺组织,也可用于治疗目的。
在核医学领域,有一些放射性核素特别适用于诊疗一体化方法,例如前文提到的131I,或镥‐177(177Lu),因为它们同时具有伽马射线和β射线发射特性。在其他情况下,可以将不同的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到同一生物分子上,前者用于诊断目的,后者用于治疗。在大多数情况下,适用于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成像的同位素是在诊断阶段更倾向于使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因为PET的空间分辨率高于常规闪烁扫描,还能提供准确的定量信息。在治疗方面,广泛使用的β发射放射性核素包括钇‐90(90Y)或 177Lu,尽管α发射体如镭‐223(223Ra)和锕‐225(225Ac)正逐渐成为有潜力的有用工具[6]。
在个体化医疗的背景下,诊疗一体化方法旨在识别患者体内的特定靶点,以制定个性化的治疗路径,并监测治疗反应。靶向治疗通过肽受体放射性核素治疗(PRRT)在神经内分泌肿瘤(NET)的管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7]。此外,诊疗一体化在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患者中也展现出令人期待的结果[8]。下文将回顾核医学中靶向成像与治疗更为成熟的应用,并概述推动诊疗一体化领域发展的前沿创新应用。表1总结了有关诊疗一体化临床应用的主要文献。
2. 分化型甲状腺癌中的碘治疗
如前所述,放射性碘治疗(RAI)是癌症诊疗一体化方法中最古老的范例。碘是甲状腺合成激素甲状腺素(T4)和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所必需的元素。在核医学实践中,常规使用两种碘放射性同位素。前者是碘‐123(123I),其半衰期为13.22小时,主要发射能量为 159千电子伏特,可用于获得高质量的治疗前后成像。后者是前述的 131I,具有β射线(约占辐射的90%,平均能量:192千电子伏特,平均组织穿透深度:0.4毫米)和伽马射线(约占辐射的10%,平均能量:383千电子伏特)发射特性。1946年,放射性核素 131I首次成功用于甲状腺癌的治疗。分化型甲状腺癌(DTC)包括起源于甲状腺滤泡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其三种组织学类型已被深入研究:滤泡状癌(FTC)、乳头状癌(PTC)和嗜酸细胞癌(HTC)[9]。手术,尤其是全甲状腺切除术,是首选治疗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最佳手术方案需考虑多种因素,如组织学类型、疾病范围以及是否存在淋巴结受累。保护邻近解剖结构(如神经和血管)至关重要[10]。
甲状腺切除术后通常进行放射性碘全身闪烁显像(WBS),以检测手术后残留的甲状腺组织以及是否存在摄碘的转移性疾病。特别是淋巴结是最常见的转移灶部位,尤其是在PTC [11]的情况下。关于RAI作为手术后清除残留组织的辅助治疗作用,根据美国甲状腺协会(ATA)的指南,治疗性放射性碘的选择应仅限于中高危受试者[12]。图1展示了一例采用 131I治疗的高危乳头状甲状腺癌病例。
对于放射性碘治疗(RAI),多年来许多中心广泛采用各种固定剂量作为经验性方法,用于治疗残留甲状腺组织或远处转移[13]。尽管根据大多数已发表的报告,这种方法使用简便且相当安全,但其严格依赖于医生的专业知识以及对最适剂量的个人判断。有报道称,“固定剂量”的经验性方法可能导致对恶性病灶照射剂量的低估,或超过安全剂量限值[14,15]。相反,个体化剂量测定旨在最大化靶区所接受的辐射负荷,从而对肿瘤产生致死效应,同时尽量减少非靶器官因非预期照射而产生的不良反应[16]。特别是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SPECT)与计算机断层扫描(CT)的融合成像技术,相较于全身闪烁扫描术,在术后精确位置甲状腺床内摄碘的残留组织或发现淋巴结转移方面提供了显著更高的准确性[17]。
2.1 诊疗一体化在碘剂量测定中的应用
从诊疗一体化的角度来看,使用 123I进行成像可用于为将接受 131I治疗的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制定个体化剂量测定方案。最近,正电子发射放射性核素碘‐124(124I,半衰期为4.2天)已被用于PET成像[18]。利用 124I进行PET/CT扫描可实现基于体素的剂量测定,从而计算靶病灶和非靶实质组织所受辐射剂量。目前关于分化型甲状腺癌剂量计算的最佳方法仍存在争议。
Klubo‐Gwiezdzinska等人对87例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进行的一项回顾性研究中比较了经验性方法与基于剂量测定的方法:结果显示基于剂量测定的方法疗效更高,且安全性特征与经验性方法相似,因此支持在高危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中采用个体化处方活度[19]。上述研究结果与Deandreis及其同事[20],报告的结果相反,后者对352例接受131I治疗的碘摄取性转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进行了回顾性评估,其中一组采用经验性固定活度3.7 GBq(n = 231),另一组则根据全身/血液清除率(WB/BC)剂量测定采用个体化活度(2.7–18.6 GBq)( n = 121),主要终点是评估两组间总生存期(OS)的差异。作者未发现两组在OS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得出结论:与固定剂量方法相比,基于全身的剂量测定并未显著改善生存率。还需进一步研究以更好地明确个体化剂量测定相对于标准固定剂量的增量价值,尤其是成本效益方面的考量[21]。
3. 间碘苄胍在神经母细胞瘤中的应用
神经母细胞瘤(NB)是儿童中最常见的实体瘤,起源于神经嵴的胚胎交感肾上腺谱系,几乎仅发生于儿童。尽管这是一种相对罕见的疾病,发病率为每8000例活产中1例,但它占儿科患者中约13%的恶性肿瘤相关死亡[22]。神经母细胞瘤可发生在交感神经系统的任何部位,但最常见的部位是腹部的交感神经节以及肾上腺的髓质部分。根据儿童肿瘤组(COG)的分类,NB依据多种生物学和临床因素被分为低、中、高风险[23]。尽管在治疗方法上已取得许多进展,高危神经母细胞瘤的预后仍然较差。
3.1 基于MIBG的诊疗一体化在成像中的应用
1979年,合成了一种去甲肾上腺素类似物,即间碘苄胍(MIBG),能够被交感神经细胞摄取。MIBG最初用核素 131I标记,并成功用于肾上腺髓质良恶性肿瘤及异位嗜铬细胞瘤的闪烁显像可视化[24]。1984年,Kimming及其同事报道了一例2.5岁女孩,患有腹部肿块并有神经母细胞瘤临床怀疑,给予131I‐MIBG后进行平面闪烁显像。病灶显示出强烈的放射性药物摄取,随后通过剖腹手术进行活检,结果证实为未分化神经母细胞瘤[25]。自此以后,MIBG被标记上 123I,该同位素具有适合闪烁显像的优良物理特性,并广泛应用于神经母细胞瘤患儿的诊断和随访[26]。特别是混合SPECT/CT的应用在患者治疗后的再分期中显示出极其重要的价值,与平面闪烁显像相比,在39%的病例中能够实现病灶的精确定位并提供额外信息[27]。
关于使用 123I‐MIBG对NB进行显像,需要指出的是,已有多种半定量评分方法被提出,用于标准化治疗前后图像的解读,其中包括所谓的Curie评分,该评分将患者身体划分为多个区域,每个区域分配0到3分的评分,以定义疾病范围[28]。在一项纳入大样本患者队列(n = 280)的4期研究中,柯里评分被用于诊断时、诱导化疗后以及自体干细胞移植后[29]对123I‐MIBG图像的解读。作者发现,柯里评分在儿童神经母细胞瘤的管理中具有很高的预后价值;特别是那些在诱导治疗后评分为> 2的受试者,其预后较差。
3.2 基于MIBG的诊疗一体化用于治疗
MIBG 是一种具有明确诊疗一体化意义的放射性药物,因为它既可以标记 123I(用于诊断),也可以标记 131I(用于治疗)。对于拟接受 131I‐MIBG 治疗的患者,使用123I‐MIBG 进行治疗前成像至关重要,可体内显示神经母细胞瘤对放射性配体的摄取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两种放射性示踪剂的生物分布在小脑摄取方面存在差异,仅131I‐MIBG 观察到小脑摄取,而 123I‐MIBG 则未见此现象[30]。尽管131I‐MIBG 也曾用于成人嗜铬细胞瘤和副神经节瘤的治疗,但131I‐MIBG 作为单药或与其他药物联合使用,在治疗复发性或化疗耐药性神经母细胞瘤儿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缓解率介于20% 至40% 之间[31, 32]。131I‐MIBG 还已成功引入作为一线治疗手段用于缩小神经母细胞瘤体积:一组44 名高危神经母细胞瘤患儿接受了至少2 个周期的131I‐MIBG 治疗,固定剂量分别为7.4 和3.7 GBq,随后根据情况施行手术,或进行新辅助化疗后手术,总体缓解率达到73%[33]。
3.3 基于MIBG的诊疗一体化用于剂量测定
此外,可根据医学内照射剂量学(MIRD)模型,基于患者体重的最大耐受剂量[34],利用诊断扫描来计算患者的剂量测定。在此背景下,使用正电子发射体124I 标记的MIBG(124I‐MIBG)结合PET/CT 技术[35] 实现精确的基于体素的剂量测定,是一种非常有前景的方法。
5. 神经内分泌肿瘤的肽受体放射性核素治疗(PRRT)
神经内分泌肿瘤(NET)是一类罕见的恶性肿瘤,年发病率为每10万人中5.86例,女性患病率较高[36,37]。NET起源于神经内分泌细胞,最常累及胃肠道(62%‐67%)和肺(22%‐ 27%)。在初诊时,12‐22%的受试者已出现转移,肝脏是最常见的转移灶部位。根据有丝分裂指数[37],NET通常被分为G1、G2和G3三类。另一个重要的分类是将NET分为“功能性”和“非功能性”。功能性NET可产生多种激素,如胰岛素、胃泌素、胰高血糖素、血管活性肠肽(VIP)、5‐羟色胺、生长抑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从而引起广泛的症状[38]。手术是首选治疗方法,但由于诊断时常处于晚期,手术并不总是可行。
神经内分泌肿瘤(NET)的特点是过表达内源性肽生长抑素的受体,生长抑素对激素释放、胃肠动力和细胞生长具有多效性抑制作用[39]。目前已鉴定出五种生长抑素受体亚型( SSTRs 1-5),它们属于具有七次跨膜结构域的G蛋白偶联受体超家族中的一个独特亚群。NET中SSTRs 2表达密度高,因此合成长效类似物奥曲肽和兰瑞肽已被批准并广泛用于 NET的治疗。
5.1 神经内分泌肿瘤影像的诊疗一体化
喷曲肽是一种合成的螯合生长抑素类似物,用放射性核素铟‐111(111In)标记,因其对 SSTRs 2具有高亲和力,对SSTRs 3和SSTRs 5亲和力较低,且对其他受体亚型[40]无明显结合,已引入临床实践用于NET成像。多年来, 111In‐喷曲肽闪烁扫描术一直是体内显示 NET中生长抑素受体(SSTRs)的非常有用的方法。最近,已开发出三种用放射性核素镓‐ 68(68Ga)标记的放射性药物用于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NET成像: 68Ga‐DOTAPhe1‐Tyr3‐奥曲肽(DOTATOC)、 68Ga‐DOTA‐NaI3‐奥曲肽 (DOTANOC)和 68Ga‐DOTA‐Tyr3‐奥曲肽类似物(DOTATATE)[41]。PET技术比使用 111In‐喷曲肽的闪烁扫描术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能够进行精确的定量计算,并且代表了一种单日检查程序[42]。
5.2 NET治疗的诊疗一体化
NET中生长抑素受体(SSTRs)的发现为靶向放射性核素治疗打开了大门,该治疗方法基于使用β发射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的生长抑素的合成类似物,特别是 90Y和 177Lu。这种诊疗一体化方法被称为肽类核素受体治疗(PRRT)。Lutathera®(177Lu‐DOTATATE)已于2018 年1月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并于2017年9月获得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批准,成为首个用于进展性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GEP‐NET)PRRT治疗的放射性药物。该疗法包括给予177Lu‐DOTATATE,分为4个周期,每个周期以固定活度7.4 GBq给药,每8周一次[43]。Lutathera®的获批之前,在过去20年中已开展了大量临床研究,旨在评估PRRT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PRRT的首次应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通过给予高活度的111In‐喷曲肽利用俄歇效应,但由于俄歇电子需非常接近细胞核才能对DNA产生作用,因此获得了不满意的结果[44], 90。Y‐DOTATOC在PRRT的首次临床实践中被引入临床。该放射性药物旨在利用90Y的物理特性(最大能量:2.27 MeV,最大射程:11 mm,半衰期:64小时),以选择性照射过表达 SSTRs 2的神经内分泌肿瘤,同时考虑到该化合物不仅能作用于靶细胞,还能通过所谓的 “交叉照射”效应影响邻近的恶性组织[45]。Y‐DOTATOC通过静脉注射给药,并分多个周期给药,直至达到最大可耐受剂量,其中肾脏为剂量限制器官,阈值为25‐27 Gy[45]。为了降低肾毒性,患者在放射性药物给药前后接受了联合输注带有正电荷氨基酸的放射性化合物。最近,已合成 177Lu‐DOTATATE并将其应用于PRRT,以利用177Lu(最大能量:0.49MeV,最大射程:2 mm,半衰期:6.7天)的特性,该同位素既是γ和β发射体,从而允许进行治疗后剂量测定研究[46]。使用 177Lu‐DOTATATE和 90Y‐DOTATOC进行PRRT在神经内分泌肿瘤中均显示出较高的客观缓解率,且毒性可耐受。
在1997年至2003年期间接受PRRT治疗的大样本队列受试者(n = 807)中,Bodei等人发现,与单独使用 177Lu相比,使用90Y或 90Y联合 177Lu治疗导致更高的肾毒性,同时报告高血压、血红蛋白和血小板毒性为其他不良反应[47]。PRRT研究的基石是III期临床试验NETTER‐1( https://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1578239),其结果最近已发表[48]。在该研究中,229名患有分化良好的转移性中肠神经内分泌肿瘤的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 177Lu‐DOTATATE联合最佳支持治疗(包括长效可重复奥曲肽(LAR))或单独使用LAR (每4周60 mg的剂量)。试验结果显示,在第20个月时,177Lu‐DOTATATE组的无进展生存率估计为65.2%,而对照组为10.8%。此外,前者的缓解率明显更高(即18%),相比之下仅接受奥曲肽的组为3%。值得注意的是,在接受177Lu‐DOTATATE治疗的受试者中,分别有1%、2%和9%出现了3级或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血小板减少症和淋巴细胞减少症。
通过将PET/CT成像与 68Ga‐DOTA‐肽类以及分子神经内分泌肿瘤转录组分析(即NETest)获得的数据相结合,将进一步改善神经内分泌肿瘤的管理,从而推动治疗向越来越个体化的方法发展。在Malczewska及其同事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评估了NETest与影像学的一致性:NETest与解剖成像(CT/MRI)的一致性为92%,与 68Ga‐DOTA‐肽类PET/CT的一致性为94%,与双模态(CT/MRI和PET/CT)的一致性为96%[49]。图2和图3展示了接受 PRRT治疗的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的临床病例。
6. 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
前列腺癌(PC)是男性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也是男性因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50]。在可行的情况下,前列腺癌的一线治疗为手术或消融性放射治疗。由于前列腺癌是一种激素依赖性恶性肿瘤,雄激素剥夺治疗(ADT)广泛用于晚期疾病患者,以及局部疾病但具有高复发风险的患者。如果在ADT治疗期间出现前列腺癌进展,则该疾病被定义为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CRPC)[51], ,这是一种侵袭性状态,对医生来说是一个治疗挑战。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的引入筛查深刻改变了前列腺癌的管理,PSA是一种由前列腺上皮细胞和前列腺癌产生的雄激素调节的丝氨酸蛋白酶。PSA检测在临床实践中的常规使用提高了早期阶段患者的检出率,并显著改善了生存率[52]。
6.1 PSMA靶向成像
针对前列腺癌(PC)的靶向成像的首次尝试是引入放射性标记单克隆抗体(MoAb)111In‐卡普罗单抗喷替肽,也称为ProstaScint®(Cytogen公司,普林斯顿,新泽西州),该抗体能够有效结合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SMA)分子[53]的细胞内表位(N端)。111In‐卡普罗单抗在多种临床环境中显示出价值,特别是在前列腺切除术或放射治疗后怀疑疾病复发的受试者中。在一个包含183名接受手术且PSA值升高的男性大样本队列中,免疫闪烁扫描术能够在60%的病例中发现复发[54]。需要强调的是,常规闪烁显像(平面显像和SPECT)的空间分辨率有限,但这一缺点可通过使用混合SPECT/CT系统部分克服[55]。在这方面,木村等人证明了SPECT/CT在原位初始治疗后复发性前列腺癌患者中检测精囊侵犯的有用性:在59名生化失败的受试者中,使用111In‐卡普罗单抗与活检结果相比,其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37.5%、88.2%、33.3%和90.0%[56]。
使用 111In‐卡普罗单抗在诊断中获得的令人鼓舞的结果推动了其治疗用途的研究:在一项I期研究中,德布及其同事采用靶向卡普罗单抗所识别相同表位的 90Y‐CYT‐356单克隆抗体( MoAb),对12例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患者进行放射免疫治疗(RIT)[57]。值得注意的是,入组的受试者中无人达到完全或部分缓解。111In‐卡普罗单抗的主要局限性在于其仅能结合PSMA的胞内区域。此外,单克隆抗体在成像与治疗中的应用因免疫原性问题而受到限制[58]。
前列腺癌诊疗一体化的一个转折点是开发了68Ga标记的PSMA HBED‐CC(即PSMA‐11),它属于PSMA抑制剂类别,能够与PSMA的细胞外部分结合,并具有令人满意的清除率和生物分布特性[59]。尽管已有多种PSMA抑制剂被引入临床实践,但上述68Ga‐PSMA‐11目前仍是PET成像中最广泛使用的放射性药物。在一项针对1007名接受68Ga‐PSMA‐11 PET/CT检查患者的回顾性分析中,该成像方法能够在79.5%的受试者中检测到至少一个提示复发性前列腺癌特征的病灶[60]。在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来自4个澳大利亚中心的431名前列腺癌患者队列评估了68Ga‐PSMA PET/CT的临床影响[61]。在这种情况下,PET/CT结果能够使 51%患者的计划治疗方案发生改变,其中在接受根治性手术或放射治疗后出现生化失败的患者组中影响更大(62%的改变),而初分期患者组中的影响较小(21%的改变)。
6.2 PSMA靶向治疗
关于治疗方面,必须指出的是,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是一种侵袭性疾病,治疗选择有限,包括化疗、使用恩杂鲁胺/阿比特龙的激素治疗,或最近引入的细胞治疗(西普鲁塞‐T)。对于有症状的骨转移患者,在注册性临床试验ALSYMPCA取得令人鼓舞的结果后,α发射体放射性药物 223镭二氯化物(多菲戈®)已最近被引入临床实践[62, 63]。然而, 223镭二氯化物不适用于治疗伴有内脏转移的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患者,因为其作用仅限于骨骼病变。
在此情况下,诊疗一体化放射性药物 177Lu‐PSMA‐617的引入为通过所谓的放射性配体治疗(RLT)管理CRPC受试者提供了一种潜在有用的新型工具。一项德国多中心研究纳入了 2014年2月至2015年7月期间接受RLT治疗的145例转移性CRPC患者,治疗周期为1‐4个,每周期放射性活度范围为2‐8 GBq[64], ,作者报告在完成所有计划周期后总体生化反应率为 45%,且毒性特征可耐受。值得注意的是,在Ferdinandus等人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发现,以SUVmax衡量的68Ga‐PSMA摄取程度并非接受RLT治疗的CRPC患者的显著疗效预测因子,这很可能是因为侵袭性病灶(即预后更差的病灶)表现出更高的PSMA水平[65]。Rahbar等人的一项回顾性研究评估了71例每8周接受3个周期 177Lu‐PSMA‐617治疗的患者对RLT的反应。在这些病例中,56%和66%的患者分别出现了PSA下降≥50%以及一定程度的PSA下降,且有相当数量的受试者表现为延迟反应,即使他们在第一周期治疗中未出现反应[66]。
Yadav及其同事最近发表的一项前瞻性单臂研究评估了177Lu‐PSMA‐617在90例经化疗或2nd线激素治疗后病情进展的CRPC转移患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66]。所有受试者均接受 68Ga‐PSMA PET/CT检查以确定是否符合RLT入组条件。在1st治疗后2至3个月及评估结束时,观察到PSA显著下降分别为32.2%和45.5%,而根据影像学和PET反应标准的疾病控制率分别为77%和71%。
上述研究表明,RLT在管理CRPC患者方面可能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仍需更大样本的进一步研究。在这方面,正在进行的III期临床试验VISION( https://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3511664)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该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比较接受 177Lu‐PSMA‐617联合最佳支持/标准治疗的进展性PSMA阳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受试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与仅接受最佳支持/标准治疗的受试者的差异。
7. 肝肿瘤的放射栓塞
选择性内照射放疗(SIRT),也称为经动脉放射栓塞(TARE),是一种针对原发性和继发性肝肿瘤的局部区域治疗方法。该疗法的原理基于肝脏独特的血液供应,即肝脏同时接受来自肝动脉和门静脉的血流。研究表明,肝恶性肿瘤主要由肝动脉及其分支供血,而非肿瘤性实质则主要由门脉系统供血[67]。在SIRT/TARE中,将嵌入树脂或玻璃微球中的β发射体放射性核素90Y通过置于肝动脉内的导管直接注入血流。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装置可用于 90Y放射性栓塞治疗,一种基于玻璃微球(TheraSphere,Biocompatibles UK Ltd.,英国法纳姆),另一种为树脂微球(SIR‐Spheres;Sirtex Medical Ltd,澳大利亚)[68]。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两种微球(即玻璃微球和树脂微球)具有不同的物理机械和活度特性,但在临床试验中发现其具有相似疗效[69]。
在纳入患者进行TARE治疗之前,建议首先进行血管造影术,以评估肠系膜系统和肝动脉床的解剖结构。确定注射部位后,通过使用锝‐99m标记的大颗粒白蛋白(99mTc‐MAAs)进行闪烁扫描术来模拟 90Y‐治疗过程,其中将一定放射性活度(即150–200 MBq)的99mTc‐MAAs经动脉内注射至选定用于治疗的动脉分支。尽管99mTc‐MAAs与树脂或玻璃微球具有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理化性质,但已有多个发表的研究表明,99mTc‐MAAs可被视为 90Y‐微球可接受的替代标志物,并被常规用于模拟其在肝脏、肺和胃肠道中的分布[70]。 99mTc‐MAAs作为TARE中预测性生物标志物的应用已得到多项证据支持。特别是,加林及其同事通过对SPECT/CT检查进行定量分析,计算了36例接受玻璃微球TARE治疗的肝细胞癌患者的肿瘤剂量测定和非肿瘤剂量测定,其中16例伴有门静脉肿瘤血栓(PVTT)[71]。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发现,在多变量分析中,递送至肿瘤的剂量是唯一与治疗反应相关的参数,而 99mTc‐MAAs在PVTT区域的摄取是反应的强预测因子。然而,为了实现TARE的个体化方法,必须考虑多个因素,特别关注肿瘤生物学、侵袭性和免疫环境[72, 73]。图4展示了一例采用树脂微球治疗的肝细胞癌患者实施TARE/SIRT诊疗一体化方法的实例。
最近,已开发出负载钬‐166的聚(L‐乳酸)微球( 166Ho‐PLLA‐MS)[74]。钬‐166(166Ho)具有适用于诊疗一体化的优良特性,可同时发射β粒子(1.77 MeV)和γ射线(80.57 keV),其半衰期为26.8小时[75]。其中β发射可用于治疗目的,光子发射则可用于闪烁显像和剂量测定分析。此外,钬‐166具有顺磁特性,因此Ho‐PLLA‐MS还可通过磁共振成像(MRI)进行成功成像,亦可用于剂量测定[76]。在1期HEPAR试验中(https://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3379844),15名伴有肝转移的受试者接受了全肝剂量为20 Gy (n=6)、40 Gy (n=3)、60 Gy (n=3) 和 80 Gy (n=3) 的动脉内166Ho‐放射性栓塞治疗。在接受80 Gy剂量的受试者中,有两名患者出现剂量限制性毒性:一名患者出现4级血小板减少症、3级白细胞减少症和3级低白蛋白血症,另一名患者出现3级腹痛[77]。因此,全肝的最大耐受剂量被确定为60 Gy。在此基础上,正在进行的2期HEPAR PLUS试验( https://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2067988)可能有助于更好地评估 166Ho‐PLLA‐MS在临床实践中的临床有效性。该研究旨在根据RECIST 1.1评估30–48名具有可测量的肝转移的患者的肿瘤反应、完全和部分缓解以及毒性。纳入的受试者将在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PRRT周期(使用7.4 GBq 177Lu‐DOTATATE)后的20周内接受额外的166Ho‐RE治疗。
8. 个体化非放射性核素靶向治疗的PET成像
除了基于放射性核素对(诊断/治疗)临床应用的诊疗一体化应用外,诊疗一体化还包括特异性生物标志物(如受体、转运蛋白)的检测,这些生物标志物可被成功用于靶向治疗。就乳腺癌(BC)而言,近年来在识别与特定肿瘤生物学和行为相关的多个分子靶点方面已取得诸多进展,例如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激素受体、胃泌素释放肽受体(GRPR)、叶酸受体(FR)等[78]。特别是,16α‐[(18)F]氟代雌二醇‐17β(18F‐FES)已被应用于晚期乳腺癌患者中雌二醇受体(ER)的PET检测。Dehdashti等人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对51名绝经后女性组成的队列进行了18F‐FES PET/CT扫描,这些患者均为晚期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并在雌二醇治疗前接受扫描;在入组的受试者中,17名对激素治疗有反应,31名对激素治疗无反应 [79]。
值得注意的是,有应答者的肿瘤中SUV值高于无应答者,因此提示使用18F‐FES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可能对激素治疗的应答具有预测价值。
另一个对乳腺癌管理至关重要的分子靶区是HER‐2。HER家族包括跨膜蛋白,这些蛋白可响应胞外信号而激活细胞内信号通路。HER2基因的扩增与更具侵袭性的肿瘤相关,其特征是高增殖率和不良预后[80]。在接受抗HER‐2治疗的患者中,检测HER‐2表达对于筛选更可能从上述治疗中获益的受试者至关重要。特别是曲妥珠单抗(赫赛汀;基因泰克,南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治疗HER‐2阳性乳腺癌的首个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曲妥珠单抗通过结合HER‐2的胞外域,已被证实可通过多种机制抑制肿瘤生长和增殖。除曲妥珠单抗外,后续还引入了其他靶向HER‐2的药物,如帕妥珠单抗(帕捷特;基因泰克,南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州)和曲妥珠单抗emtansine(T‐DM1),其中曲妥珠单抗与DM‐1连接,DM‐1是一种强效的微管聚合抑制剂[81]。
然而,有研究指出,许多最初对抗HER‐2治疗有反应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由于HER‐2表达缺失而产生耐药性。为了识别接受靶向治疗患者的HER‐2表达缺失情况,需要进行重复活检。在此情况下,通过影像学方法在靶向治疗前和治疗期间评估HER‐2 status 将极为重要,不仅有助于患者筛选,还能早期识别获得性耐药,从而及时将无应答者转换为更有效的治疗方案,并避免重复活检的需要。为此,已将曲妥珠单抗用放射性核素锆‐89(89Zr)标记,该核素具有良好的空间分辨率,半衰期为3.27天[82]。
89Zr较长的物理半衰期使其特别适合匹配抗体的生物半衰期。89Zr与单克隆抗体的连接通过一种特定的螯合剂——去铁胺实现。B (DFO)[83]。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ZEPHIR试验,这是一项从比利时和荷兰招募患者的多中心研究[84]。该研究纳入了56名经免疫组织化学或原位杂交证实为HER‐2阳性的转移性乳腺癌女性患者,在接受T‐DM1治疗前均进行了使用 89Zr‐曲妥珠单抗的PET/CT扫描。值得注意的是,使用 89Zr‐曲妥珠单抗的PET检测出39例患者存在HER2阳性病灶,其中28例对T‐DM1治疗产生应答。未来仍需开展纳入更大队列的进一步研究,以验证使用89Zr‐曲妥珠单抗作为诊疗一体化显像剂在转移性乳腺癌中的应用价值。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是靶向治疗中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生物标志物。EGFR的异常激活或表达已在多种上皮性恶性肿瘤中得到证实,例如结直肠癌和肺癌。在此背景下,使用 SPECT或PET探针进行分子影像在转移灶中对EGFR表达的体内识别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放射性标记的单克隆抗体如64Cu‐DOTA‐西妥昔单抗和111In‐DOTA‐西妥昔单抗存在若干局限性[85]。在这一特定领域,一种基于适配体技术的创新方法有望为EGFR状态的体内成像提供有用的工具[86]。
9. 结论
核医学中的诊疗一体化旨在通过使用相同分子(或尽可能相似的分子)将诊断与治疗相结合,这些分子可标记不同的放射性核素,或在不同剂量下使用相同的放射性核素。这种治疗方法与个体化医疗的概念密切相关[87] ,其重点不在于疾病本身,而在于根据拉丁语“persona”所理解的患者个体,而该词又源自希腊语“πρόσωπον”(prosopon)。值得注意的是,在古希腊剧场中,“πρόσωπον”一词也用来指演员面部佩戴以诠释特定角色并向观众象征特定情绪状态的“面具”。在这种“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中,诊疗一体化旨在揭示疾病的“ πρόσωπον”,从而提供有关特定靶点存在及其生物分布的宝贵信息,以便根据患者的特定特征(如受体或转运体表达、基因组分析、免疫状态等)实现个性化治疗。
还需进一步研究来更好地了解这一创新方法在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方面所能达到的程度,包括成本效益问题。
10. 专家观点
在“诊疗一体化时代”的初期,重点在于结合技术和文化的进步。特别是,持续对 SPECT/CT和PET/CT装置进行技术更新对于实现影像学生物标志物的高灵敏度检测、提供准确的定量数据以及满足个性化剂量测定的需求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新型数字PET/CT装置有望推动该领域的发展。在一项最近发表的回顾性研究中,一组88名接受 68Ga‐PSMA‐11显像的前列腺癌男性患者使用数字PET/CT(dPET/CT)进行检查,并与另一组88名受试者匹配临床参数,后者使用相同的放射性药物但通过模拟PET/CT(aPET/CT)进行检查88]。研究发现,与aPET/CT相比,dPET/CT能够检测到显著更多的病灶,尤其是在PSA值较低的受试者中。
必须认识到,诊疗一体化是一种革命性方法,为核医学带来了独特的发展机遇。在此背景下,需要一种范式转变,即核医学必须将自身定位在治疗与影像的交汇点上。迄今为止,核医学的教育培训主要集中在诊断和技术方面,尤其侧重于融合PET/CT和SPECT/CT成像。核医学界必须努力提升其临床文化和多学科参与水平,以期不是被动地旁观,而是积极促进正在进行的“诊疗一体化革命” 89]。
9.1 五年展望
放射性药物学是一个预计在未来几年内快速发展的领域。在这方面,放射性核素铜‐64(64Cu)在科学界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铜是涉及细胞分化、新陈代谢和生长等多种代谢过程中的必需元素。此外,人类铜转运蛋白1(CTR1),一种负责铜细胞内摄取的跨膜蛋白,在许多恶性肿瘤中被发现过度表达。64Cu是一种回旋加速器生产的放射性核素,具有中等半衰期(12.7小时),通过正电子和β粒子发射衰变,使其适用于诊疗一体化应用。放射性药物 64CuCl2,作为CTR1的底物,目前正在研究中,在黑色素瘤或前列腺癌等肿瘤的多项临床前和临床试验中显示出良好的结果前景[90,91]。
需要指出的是,α发射体在诊疗一体化中的应用是另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领域。事实上,在靶向α治疗(TAT)方面,目前唯一获批用于临床的放射性药物是前文提到的 223Ra‐二氯化物[62]。尽管与β粒子相比,α发射体的穿透范围较短,但其具有多个引人关注的特性,例如能够引起DNA双链断裂、在有丝分裂时导致严重的染色体损伤(如染色体碎裂)和复杂的染色体重排、不依赖于氧合状态破坏肿瘤细胞,以及克服对β发射体耐药的潜力[92]。使用 213Bi‐DOTATOC的TAT正在为对177Lu‐DOTATATE [93]耐药的神经内分泌肿瘤治疗提供初步且令人鼓舞的结果。此外,采用225Ac‐PSMA‐617的放射性配体治疗正在作为 177Lu‐PSMA‐617[94]的替代方案,用于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患者管理的评估中。然而,仍需设计良好的多中心研究并纳入更大的队列,以进一步评估TAT在诊疗一体化领域的临床影响,特别是关于毒性和不良事件的发生率[95]。
最后,诊疗一体化的发展将推动对新生物标志物和探针的研究。在这方面,前文提到的 EGFR是创新性诊疗一体化方法的一个非常有前景的靶区。在此领域中,已引入了一种名为适配体的新技术。适配体是单链DNA/RNA寡核苷酸,可通过指数富集的配体系统进化( SELEX)技术获得[96]。据报道,适配体对靶区具有高度特异性,并表现出低免疫原性。就 EGFR而言,最近开发出一种18F标记的RNA适配体,在表达不同水平EGFR的小鼠肿瘤模型中显示出高度选择性的靶向能力。尽管该方法仍需通过进一步研究加以验证,但可以合理推测,它将在未来成为诊疗一体化研究的一个扩展领域[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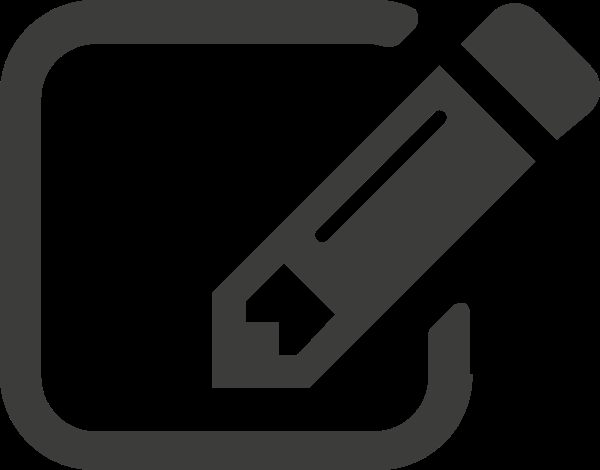























 34
34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