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3日,我们邀请
来知乎举办一场关于投行的Live~
投行在大家心中或多或少都有一层神秘的光环。
对于在校学生,大家对投行的了解多是来源于校友、媒体和一些就业机构。
与许多影视作品和八卦传闻不同的是,真实的投行世界可能会少一点浮夸,多一点残酷。有成就,也有疲惫…
本次 Live 中,我们会聊到投行内部各部门的分工、投行的内部晋升制度,并在求职准备和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给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具体内容可以参考大纲哦。
2017年12月
分享下我司学霸大牛的工作体验~
作者简介:
,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院,2005 年成为高盛第一批国内招收的应届毕业生,供职于高盛东京及香港分部12+年。作为高盛交易部门的策略师,先后参与了固定收益部,股票部和信用部三大业务线的各种价值投资和量化投资。


春 (2005.07 – 2008.07)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我进入那家传说中的投行也算是件挺幸运的事。
2005年是高盛东京在中国第一次校招,那时候国内对于“投行”的了解还处在萌芽状态,如果不是金融专业的学生,听过那些大名字的人寥寥无几。
但专业光鲜的宣讲会,在穷学生看起来无比诱人的薪金,入职以后海外培训的机会,加上“华尔街”的诱惑,那个offer就像是一张通往新世界的机票。
坐上飞机到了自由女神的国度,我的投行之旅从纽约3个月的培训开始。
各种肤色,各种背景,夹杂着各种方言的英语,高盛纽约着实海纳百川。回头去想那3个月的时间,也许是我12年工作中最轻松、最享受的3个月。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考试和项目要完成,但是周围是一群年龄相仿,初出茅庐,斗志昂扬的新生力量,加上各种“wallstreet”的洗脑和拿着公司卡可以免费出入纽约各大博物馆的优越感,让我像是在春天一样和风习习,生机盎然。
培训之后回到东京,工作算是正式开始。
2005年-2007年是全球经济历史性高增长的3年,也是这些顶级投行收益达到巅峰的时期。
我当时进入的是市场风险(market risk)部门,这个部门主要负责计算公司的整体市场风险,发现各种潜在的高风险的头寸,并从公司层面来控制因市场变动可能引发的损失。
当时全球市场的活跃度非常高,各种新型的金融产品和架构层出不穷,公司内部培训的话题都让人觉得眼花缭乱,困境债(Distress Asset),房地产信托基金(REITS),PRDC……各种名词扑面而来。
我记得进入公司负责的第一个项目是关于一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因为是一个投资框架还不完善的市场,需要明确各种风险因素,梳理历史数据及因素之间的correlation,建立VaR Model、压力测试来评估整个业务的市场风险。
工作的第一个月每天平均晚上10点回家,但是觉得无比充实,每天都能学到新的东西,成就感爆棚。
之后又参与了一个金属商品的项目,让我对基础金属和贵金属相关的产品,定价和市场风险的来源,以及有哪些规避的工具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到最后就轮到最复杂的结构化产品了,PRDC,FX TARN的市场风险计算和控制,诸如此类。
在风险部门的2年多时间,让我从一个金融小白到对各种金融产品言之成理。这个过程虽然辛苦,但那个时候的成长就像接受了春雨洗礼的劲草,拔地而起。
夏 (2008.07-2011.07)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在高盛的夏天,是短暂酷热后的一场暴雨。
第一声惊雷是2008年9月雷曼破产的消息,我记得当时我在意大利和朋友度假,每天听到的新闻大部分是道指又下跌了多少,今天又有几家银行和企业被政府bailout,又有多少人失业。
在旅馆里看新闻的我们还打趣说,不知道我们回去了公司还在么,或者我们是不是已经失业了。
我当时刚刚转到基本面策略团队(fundamental strategies team)不久。这个组隶属股票部门,主要研究基于股票基本面的一些交易策略,属于自营部门。
雷曼倒闭之后的市场一片萧条,黑天鹅效应下的对冲基金 频频倒闭,加上政府bailout之后开始大范围的加强监管,包括后期出现的Dodd-Frank,volcker rule,投行对于自营部门大幅裁员,当时的团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2008年底到2009年初,是暴风雨之后的一片狼藉,基本上每几天都会发现一些同事“消失”,在那段时间接到大老板的电话,大家都会习惯性的收拾一下桌上的自有物品,因为这次会面之后,也许就再也回不来这个desk了。
2009-2010年的公司气氛和前几年明显有了很大的区别,“风控”和“低调”成了新的关键字。大部分的新项目是与监管汇报相关的,关于投行最多的新闻是起诉案,大家讨论最多的是我们是在V型周期的最低点,还是U型周期的最低点,或者这次的周期就是一个L型。
在日本工作5年之后,我在2010年的6月申请转到了香港公司。
香港和东京虽然同属亚洲地区,但办公室的风格有很大的区别,相比较而言,香港办公室的人员更多样化一点,中国人的优势也更加明显一点,加之2011年的日本地震之后,整个亚洲的金融重心开始向香港和新加坡转移。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香港的金融行业也慢慢的瞥见了一丝彩虹。
这个夏天是一个雷暴不断的夏天。在这段时间里,更多的成长来自于对这个行业之于整个经济体系的更为切身和深度的体验和理解。
秋 (2011.07-2014.07)
从“量化”到“质变”
转到香港之后,我算是真正的开始接触量化,启蒙老师是当时香港的一个MD交易员。他在2008年初开始做空市场,到年底的时候一共为desk贡献了近1亿美金的利润。
工科出身的他属于比较nerdy的交易员。他自学python,在家里花百万港币买一套RAID的机器跑各种人工智能的程序,业余时间研究比特币和区块链 。
帮他做了一些小的项目之后,他开始让我回测和实现各种不同的交易策略。从简单的套利策略,例如指数套利(index arbitrage)——原理简单,难度在于对每个市场的交易细节的理解和底层执行系统的优化程度;到相对复杂一点的基于统计的套利策略,例如基于协整的配对交易(co-integration based pair trading);也有基于特定市场的套利策略,例如基于某个国家市场独有的single stock future的多空策略。
开始做策略的时候,试下来几个主意的结果都差强人意,要么是收益不够高,要么是波动性 太大造成sharpe ratio不理想,抑或是回撤或者交易成本太高使得整个策略只能是纸上谈兵。但随着做的时间长了,渐渐会发现一些规律和应对方法(比如止损逻辑(stoploss logic),市场中性(market neutral),信号整合(signal combination),等等),感觉也就慢慢的培养起来。
接触量化之后,对我个人而言,是个“质变”的过程。
一方面,我开始深入地研究各种理论,包括时间序列(time series),组合管理(portfolio management),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等,把以前学到的各种统计和金融知识更好的融合在一起。而另一方面,我也开始注意到市场和实现方面的细节,比如如何计算交易成本,有哪些市场可以做空,哪些产品可以做对冲,如何利用市场的不够有效等等。
量化本身也是个涵盖很广的概念,包括发现并利用错误定价(mispricing)的套利策略,到利用硬件提高速度的高频策略,直到寻找规律(pattern)进行预测的智能策略,需要的是对于市场本身和理论本身的深入理解和交汇融通的过程。基本上所有的量化策略都需要不断的调整和优化,因为市场本身也时时刻刻发生着变化。
在高盛的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
冬 (2014.07-2017.07)
梅花香自苦寒来
在这个股票部门做了将近4年的时间,2014年初公司开始要在亚洲做公司债 的自动化交易。为了尝试一下新的资产类别,我又转到了信用(credit)部门。
公司债本身受微观和宏观的双重影响,一方面要考虑宏观利率的变化对其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要考虑公司本身微观环境的信用评级。定价的复杂性和流通性 的限制,使得公司债只可以在OTC市场上交易,这一个特质让公司债和股票交易差之千里。
在信用部门做的最有趣的项目是将债券的买卖单和潜在的对手相匹配,这个听起来很容易的事情,却因为亚洲债券市场缺乏统一的信息中心而成为一个难题,原则上每个OTC 合同只有交易双方知道彼此信息,所以对于一个从未交易过的债券订单或者只有单边历史信息的订单,公司本身无法从已有信息判断谁可以做新订单的对手。
通过调查研究,我们最后采用了类似亚马逊图书推荐系统的协同过滤(collaborative filtering)算法来寻找潜在匹配,如果客户A买了A债券的同时也买了B债券, 那么与客户A有类似行为的客户B也有可能对A和B债券感兴趣。
这个项目让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其实进入了一个新的互联网+时代,虽然金融行业因为本身专业门槛高的原因,是比较晚被“侵入”的行业。但是我们仍可以看见Fintech在各个领域或迟或缓,或深或浅的渗透。
从2005年研究生毕业,在这家投行经历了10年的摸爬滚打。感觉错过了互联网黄金时代的我,在2015年9月份的时候申请了3个月的休假,在创业公司的圣地旧金山做了一次彻底的市场竞调。
SFO基本上每天都有各种各样与科技创新相关的会议,游走其中,感觉与在香港完全不同,在西海岸的这个孵化中心,科技驱动一切。带着各种感触和心得回到香港,进入Fintech创新公司成了我的一个新的目标。
2017年6月份,我终于如愿以偿的加入了云锋金融 ,开始了我的Fintech之旅。
梅花香自苦寒来,回首在高盛的12年,这段经历异常珍贵。走完传统金融的最后一季,我期待着在Fintech行业的第一个春天。










 这篇博客由一位曾在高盛工作的员工分享了其从2005年加入高盛到2017年的职业生涯,详细描述了在投行内部的不同部门工作经历,包括市场风险、股票部门和信用部门。期间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转型和挑战,最终转向金融科技领域。博主分享了在量化交易策略、风险管理以及金融市场理解上的成长和感悟。
这篇博客由一位曾在高盛工作的员工分享了其从2005年加入高盛到2017年的职业生涯,详细描述了在投行内部的不同部门工作经历,包括市场风险、股票部门和信用部门。期间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转型和挑战,最终转向金融科技领域。博主分享了在量化交易策略、风险管理以及金融市场理解上的成长和感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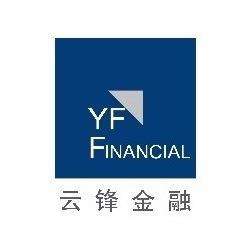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