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健
2010年5 月15日晚,香港中乐团在上海音乐厅举行了访沪音乐会。作为“2010 上海之春”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乐团选取了四部由当代作曲家创作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包 括郭文景的《滇西土风三首》、罗永晖的琵琶与乐队《千章 扫》、何占豪与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民 乐版,吴大江编曲),以及程大兆的《黄河畅想》。 音乐会的上 座率接近爆满,观众反响热烈,以雷鸣般的掌声多次要求返 场。当天的演出最后在《射雕英雄传》和《赛马》等三首返场 乐曲及观众的欢呼声中结束。
香港中乐团这次访沪音乐会的圆满演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从音乐的创作、演出,再到音乐家参与,牵 涉了提升文化产业的问题,也深入到弘扬民族音乐的思考。 如,有评论疾呼民乐要“亢奋”才有“ 出路”、回归“旋律”;另 一些则对音响的“层次”与“厚重”感推崇备至。
对此,笔者试从该音乐会的几部作品的创作思维与音响 效果入手讨论,围绕“音乐的参与”、“民乐的出路”,以及其 他相关问题,阐述香港中乐团这次访沪演出的启发。
音乐和音乐会的参与
当晚,上海音乐厅一千一百多个座位接近爆满以及全场 观众的热烈反响,力证着香港中乐团这次访沪演出的圆满,并为业界“如何增加票房”提供了诸多启发。这折射至学术界中,笔者认为则是关于“音乐和音乐会的参与”问题。
音乐的参与来自艺术作品与听赏者的心灵互动。音乐会 的参与主要由上座率体现,无论购票抑或是送票,二者显然相 区别。在现场演出中,虽然先有音乐会的参与,但却往往由前 者起主导作用。
“音乐的参与”主要涉及曲目的创作构思。
从上演作品的选取来看, 香港中乐团把观众对音乐的参 与放在首位。具体的参与手段包括让观众与乐团互动以及在 音乐形式方面凸显旋律、律动这些音乐的第一参数,使观众易 于获得听觉感知。
“互动”是“参与”的最直接手段,亦是当代艺术最常用的 手法之一。当晚,音乐会的两次高潮都有赖于观众与乐团的“共 同合作”。 第一次是《黄河畅想》中的拨浪鼓与打击乐的“对 话”。每位观众在进场之时都获发一个拨浪鼓,具体的击鼓与制
音方式在音乐会之前还实行了“预演”;第二次是返场曲目《射雕英雄传》的“吼”、“哈”呐喊声的介入。当这首家喻户晓的主 题曲响起时,观众已自发参与至其中。在指挥的“ 明确提示”下, 全场观众整齐而洪亮的呐喊声成为音乐不可或缺的 “ 伴奏”之 一。随着互动的加入,观众的情绪与音乐一同进入高潮。
在音乐的形式方面,上演的曲目较为注重听觉感知。音调与节奏是音乐的听觉感知第一参数。保留旋律线条的主导地 位以及强化律动的写作, 都是当晚多个作品抓住听众耳朵的 有效手段。《梁山伯与祝英台》、《赛马》和《射雕英雄传》直 接以脍炙人口的旋律作为主题;《滇西土风三首》以贯穿“不 发展”的固定音调为特点;《黄河畅想》不时流淌出优美的民 歌曲调……而律动的凸显既是《滇西土风三首》与《黄河畅 想》强化听觉感知的主要手段,也是整场音乐会“现代气息” 的重要体现。特别是由复节奏有机组合的打击乐,其丰富的点 状音响与鲜明的旋律线条交相辉映,成为当晚演出作品的又 一突出的共同特点。
而“音乐会的参与”,则是包括创作、演出乃至其他更多 因素的综合讨论。
首先,在选曲方面,香港中乐团在“ 传统 ”与“ 现代”、 “ 经典”与“新作”,乃至“严肃”与“流行”之间取得了很好 的平衡点。既满足一般听众对“可听性”的要求,也满足了专 业音乐爱好者的“猎奇”心理。
另一方面,这些作品不论语言风格,都有着一个共通之 处—— 作为“载体”的音乐。《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千古爱情 故事为“主题内容”,这也是其历演不衰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 因;《射雕英雄传》中豪迈的武侠情怀家喻户晓,每当其主题 曲奏响时,罗文与甄妮的对唱已萦绕于听众脑海;《赛马》律 动的音响拟态昭然揭示作品主题;《滇西土风三首》与《黄河 畅想》都建构于简练的民歌素材之上,并以之作为风格定位; 而最“现代”的《千章扫》亦在努力“ 阐释”中国书法,以架起 与观众沟通的桥梁。也许可以说,这种或直接或间接的“载 体”思维,完全切合中国听众的审美心理。因为中国听众总喜 欢听到音乐的“ 内容”,并赋予具象的联想。
其次,本次音乐会充分利用了名人效应。无论是四位赫赫 大名的作曲家,抑或是享誉世界的小提琴演奏家诹访内晶子, 以及她手上的世界名琴“海豚”(Dolphin),都让节目单熠熠生辉。
最后,一如音乐会后指挥阎惠昌所言,“世博”是这场音 乐会的特殊背景;同时,音乐会作为“上海之春”的组成部分, 香港中乐团作为申城的访客。这些都共同成就了当晚演出的 圆满成功。
一场音乐会成功与否,在于其是否能让听众“ 陶醉”。 在 今天,这须“音乐的参与”和“音乐会的参与 ”同时到位。而 且,便于促成下一次音乐会的参与。
民乐的出路
再次回到音乐作品的创作问题。香港中乐团的访沪演出 以全场观众的热烈情绪达至顶峰而圆满结束。请问:民乐一定 要“亢奋”才有出路吗?
除情绪以外,当晚的“亢奋”是由大型的民族管弦乐队来 完成。其音响层次鲜明而圆润饱满。乐队释放出来的能量几近 可与西洋管弦乐队相比。即,犹如西洋管弦乐队的音响那般 “ 立起来”。 再问:民乐是否一定要“西化”?
显然,“亢奋”与“西化”是香港中乐团这次圆满演出的 突出特征。但这并不代表这是民乐“复兴”的唯一路子。正如 上文的讨论,音乐会的参与,以音乐的参与为本;音乐的参与, 在于作品的构思设想及其内在形式的表达。笔者认为,“ 亢 奋”与“西化”的“成功”,并不是指示着民乐的出路,反而在 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中国传统民乐乐器的不足、民族器乐创作 的局限,以及当下中国听众的审美取向。
(一)关于民乐作品音乐会的“亢奋”
香港中乐团选取的曲目以壮阔、热烈的情绪为主。如此 “ 情绪”,常伴有较快的速度和清晰的拍点,和乐队整体能量 释放等特点。从开场作品《滇西土风三首》“开天辟地”般的 震撼,到返场曲目《赛马》行云流水般的得意,整场音乐会高 潮迭起,观众兴奋不已。即,这些作品常常通过整体音响较大 的强度,来刺激观众听觉神经,从而促成观众对音乐的参与。
如此方式虽然“直截了当”地带动了观众的情绪,但亦存 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音乐过多“ 哗然”会致使观众的 听觉疲劳,高度的兴奋会使感知变得迟钝。笔者以为,压轴曲 目《黄河畅想》的唢呐独奏段是整场音乐会最漂亮的一段。因 为在那一时刻,整个音乐厅终于安静了下来。而且,终于听到 了真正属于中国的旋律与音乐空间……
以“亢奋”来促成听众对“音乐会的参与”,这一做法几 乎是每一场音乐会带动观众情绪的最常用手段。因为“参与 音乐会 ”的价值就在于现场的体验;观众的“ 兴奋”,往往是 获得音乐体验的突出表现。
然而,不同类型、性质的音乐会有着不同的撩动观众心弦 方式:爵士的“亢奋”迥异于贝多芬专场的“振奋”;《春之祭》 对听觉神经的刺激亦跟京剧锣鼓对耳膜的震动截然不同。观众 自然也有不同的“兴奋”表现,或是随乐哼唱打拍,或是屏息后 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些都不能用“亢奋”一词概而了之。
而且,“亢奋”不是促成观众“参与音乐”的唯一方式。
“ 亢奋”以凸显律动、增大音响强度为主要手段。它之所 以能使听众更为容易地“参与音乐”,是因为律动与强度能为 听众营造一个“近距离”的“音响空间”。 这一点以流行音乐 为典型。但是,舒缓、悠长、安静的音乐所营造的“遥远”也常 获得“集体共鸣”,即便是流行音乐也是如此。
因此,“亢奋”不应是民乐的唯一出路。
中国民乐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音乐文化,应当具有极 为广博的语言和内涵,以及顽强的生命力。这是拥有再多“票 房”的流行音乐,或是冠以各种创新“名堂”的先锋音乐永远 无法媲美的。但当下的民乐作品常有赖于所谓的“亢奋”来获 得“音乐和音乐会的参与”。这种现象一部分应归因于大多数 中国听众的心理。因为在这个也许看戏的比听音乐的多、参与 音乐的没钱参与音乐会的环境下,“ 亢奋” 也许可以先促成 “ 音乐会的参与”,作为“音乐参与”的过渡。而另一部分原因 是民乐乐器构造上的不足。这造成民族器乐常给人以 “ 弱、 小”,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错觉。如,民乐队音色的统一就是 一个问题。所以香港中乐团的胡琴改革所努力的不只是为了 环保,更是适应当今耳朵的改进。
此外,笔者认为,大多数传统的民族器乐创作思维仍有所 局限,无论是几乎只依赖感性的“传统”写作方式,抑或是有 些迷信于西方理性的“现代”写作方式。特别是后者,仿佛对 西方的技法带有点过于崇拜。
(二)关于民乐创作的“西化”
上文已提到,民乐乐器形制的相对“弱、小”造成了对西 方“洋枪大炮”的“能量”的“膜拜”。 这种技术的“膜拜”不 仅体现在乐器的改造上,更体现在创作技术及思维的“西化” 之上。从而形成中国民乐要么走进了欧洲实验剧场,要么在上 演 “ 美国好莱坞电影大片”——以炫弄技术来获得视听感 受——的现象。
的确,本来主张“天人合一”的民乐被搬上西方人用四堵 墙围起来的舞台,中国人除了要花费巨大力气把民乐乐器 “ 现代化”以外,还得想方设法去“填充”音乐会既定的时间, “ 填充”封闭的音乐厅,甚至需要教育听众,“填充”其荒芜的 音乐心灵。
西方人在音乐方面仿佛比中国人“进步”得多,无论在乐 器演奏技术方面,还是创作技术方面,抑或是对音乐审美的思 考方面。于是,斯波索宾的《和声学》成为基本教材,《春之 祭》成为配器“圣经”,贝里奥十三首《序列》成为创作必翻 的“词典”… …
不得不承认,我们学院派的作曲学生几乎都是由西方的 音乐文化哺育长大。因此,拿起中国的五声性曲调,我们就将 其分解、变形、模进;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当下中国听众的耳 朵也已经“西化”(“现代化”)。于是,北京奥运的《春江花 月夜》依赖大量的模进转调来延展音乐,音乐会返场的常是 《赛马》,而不是《二泉映月》。
笔者认为,香港中乐团当晚演出的曲目渗透着多种西方 (现代)音乐的创作思维。听众所熟悉的不仅仅是打着民乐乐 器和打着“ 中国”标签的音乐素材和语汇,更重要的还有已经 习以为常的音乐构建思维。包括“块状”与“填充”、“高潮”、 “ 中心”,以及“场景”等西方音乐的思维模式。
“ 块状”与“ 填充 ”的音乐思维模式主要体现在固定音 调的循环重复、模进等手法。前者是《滇西土风三首》与《黄 河畅想》的共同特点。虽然二者其都采取完整的民歌作为固 定音调,但其展现的并不是中国旋律音调间的抑扬顿挫,而 是将旋律整体作为“块状”音响的“填充线条”而存在。再加 上作品所释放的巨大音响能量、节奏的强化、多调性,以及大 量对置手法的运用,使人不由得想起斯特拉文斯基的“ 原始 主义”。
“高潮”是西方浪漫主义的典型特征,作为能量释放的体 现,指示着情绪夸张起伏的顶点,并在音乐作品中起着结构信 号的作用。当晚演出中高潮迭起的“亢奋”有些类于 20 世纪 之交西方晚期浪漫派及其延续的写法——对能量的崇尚。这 尤其体现在大乐队形式以及夸张的音响强度起伏和对比之 上。如果说中国的听众还长着“ 肖邦 ”的耳朵,那么当晚的 “ 拉威尔”与“斯特拉文斯基”还是比较前卫的。
对音乐的“ 中心”的处理亦是当晚演出作品“西化”的又 一特征。这突出体现在被誉为“地心引力”的调性中心方面。就 返场曲目《赛马》而言,附点节奏和织体音型都与旋律音高的 主属张弛指向相一致,共同强调对某一“终点”(中心)—— 仿 如西方传统油画的“三维透视”焦点——的期待。这迥异于 《二泉映月》 中国式的 “ 散点透视”——不断地转移音高重 心。同样是“传统”,除了情绪的区别,选择前者恐怕亦是出于 对当下听众的“西洋耳朵”的考虑。
“场景思维”虽不专属于西方音乐创作,但由于 20 世纪 初西方舞剧配乐开始脱离表演而独立,音乐创作出现了对置、 截断、复合等蒙太奇手法。这些音乐延展方法在《滇西土风三 首》、《千章扫》和《黄河畅想》中大量存在。而《黄河畅想》 在模进、截断的使用痕迹尤为突出,甚至出现了多种风格杂糅 的现象,让人不禁联想起 20 世纪以来西方舞剧音乐的创作。
一百多年来,西方音乐的创作技术得到巨大发展,促成了 当代音乐的“百花齐放”局面。中国人“追随”西方的脚步亦 受益匪浅,无论是西洋管弦乐技术的发展,抑或是中国民族器 乐的“进步”。
然而,当我们对西方音乐创作技术仍处于“消化过程”之 时,“领路”的西方人已经找不到自己了。于是,他们一如一百 多年前德彪西、毕加索参与世博的做法,继续把目光投向“第 三世界”来搜寻各种新的音乐元素。譬如,中国民乐。如此一 来,中国当代音乐的创作——包括现代民乐的创作—— 亦随 之将民乐器乐作为独立的素材和音色标签加以运用:虽然哼 着五声音阶,但骨子里的实为西方的展演思维。
中国民乐的“ 西化”,无论是“ 两根弦”对“ 四根弦 ”的“ 追慕”(二胡改革),抑或是给五声曲调配个功能和声(或是 所谓的现代和声)都已既成事实。现状如此,相信将来更为如 此。当然,“混血儿”仿佛也没有什么不好。正如西方人学民乐、 学书法,中国人也听管弦乐与学画油画。“地球村”里住的肯定 是“世界公民”。 只要“世界公民”去听“世界音乐”即可。
笔者只是在想,我们从西方人那儿“拿来 ”的,不应只是 技术的精华,还应汲取其思维的精髓—— 从浪漫主义的表现 自我,到 20 世纪的各种实验,西方音乐的发展仿佛常常贯穿 着“寻找”的核心。也许正是这份对“寻找自己”的执着,促成 了其今天的多元并置及我们“青睐”的“遥遥领先”。
其实,中国的专业音乐不乏其“探索”努力,无论理论研 究,抑或是创作实践。但唯恐当下的现状主要是音乐学科各自 埋头苦干,互不“沟通”。结果理论界不是纠结概念界定,就是 忙于谱写民族志;创作的不是绞尽脑汁在国际比赛上获奖,就 是奔命于应用音乐的委约。最后,所谓的音乐评论笼统地高呼 一句“旋律万岁”,把艺术家们的探索全盘否定。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成功不只是因为拥有旋律,而是因 为其旋律拥有中华民族线性思维的特质—— 既凝结着精致的 音调回旋(譬如,那个优美的八度跳进),也凝结着千年传奇 故事的人文情思。其至今仍久演不衰,给予我们的启发不仅是 认识到中国人要听旋律,而是要用当下的理论去深入分析,主 题句的那个“八度”为何如此“迷人”?进而思考,今天我们又 如何用崭新的语言重构经典线条上的凝结?
其他相关问题与小结
最后再小议两点其他相关问题。
香港中乐团这次访沪演出,带来的不只是一场圆满的音 乐会,还带来了他们关于“本土标签”、企业制度等理念。
第一,鲜明的“本土”意识。该音乐会给人留下最深刻的 印象之一就是“香港制造”。 这一方面来自于“环保胡琴”的 专门介绍,也来自于返场曲目《射雕英雄传》的演出。前者体 现香港作为一个先进的国际化城市,“环保意识” 深入民心; 后者展现了香港流行乐坛黄金时期的辉煌。
第二,企业制度。香港中乐团三十余年累积了一千八百多 首委约作品,其中 40%为本土作曲家而作。这种做法类似于国 外商业演出的乐团,通过不断更新曲目,增加挑战来提升演奏 员水平。如此做法还大大促进了本土音乐创作,对音乐文化的 发展颇有裨益。
综上所述,香港中乐团在“2010 上海之春”的访沪演出具 有很大启发意义。他们的圆满演出,不仅成功做到“音乐会”与 “ 音乐”的参与,更是为中国的听众“陶醉”与艺术家们“寻找” 的“共处”构建了一个平台,为中国民乐的发展做出巨大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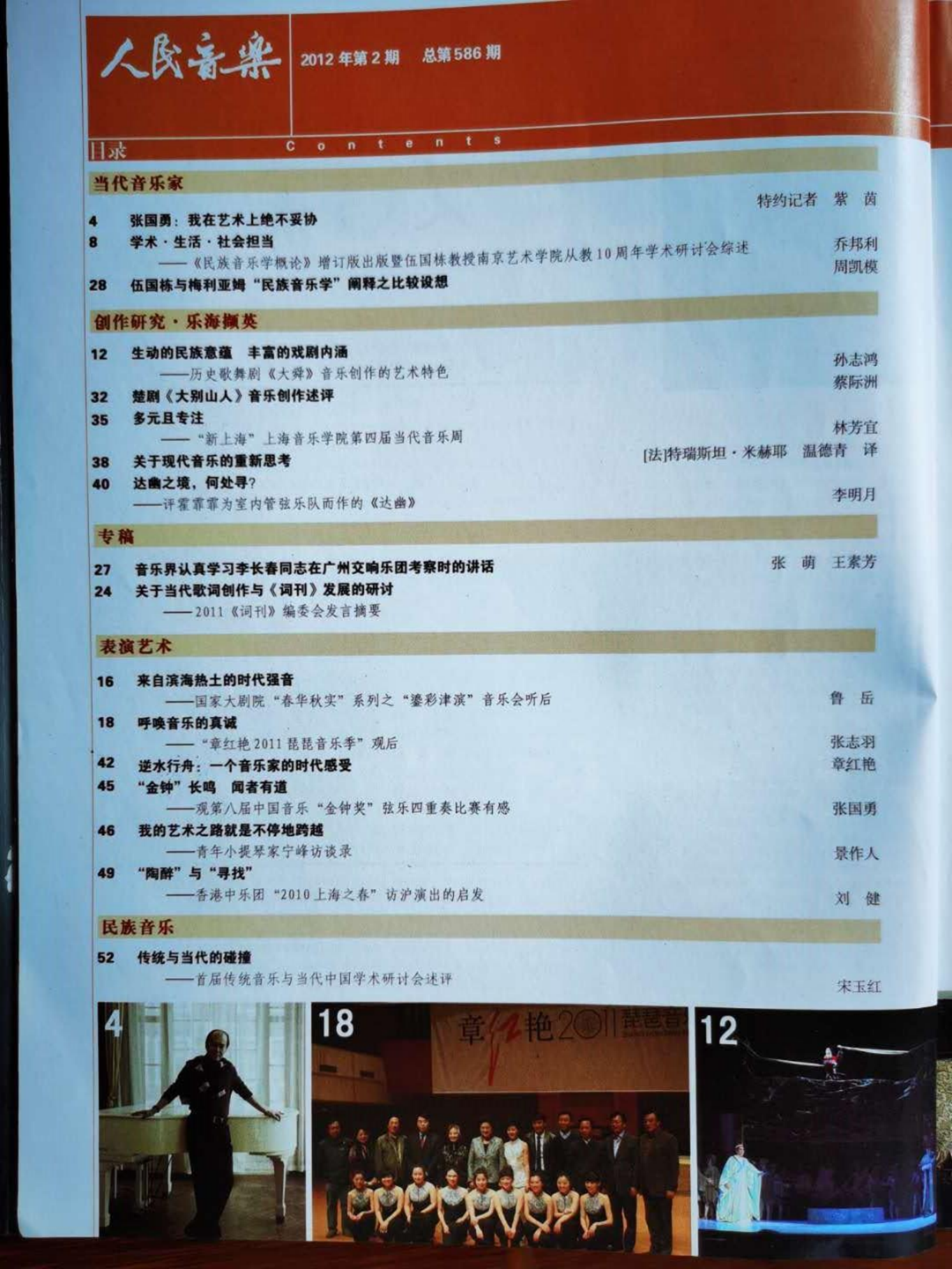

























 1万+
1万+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